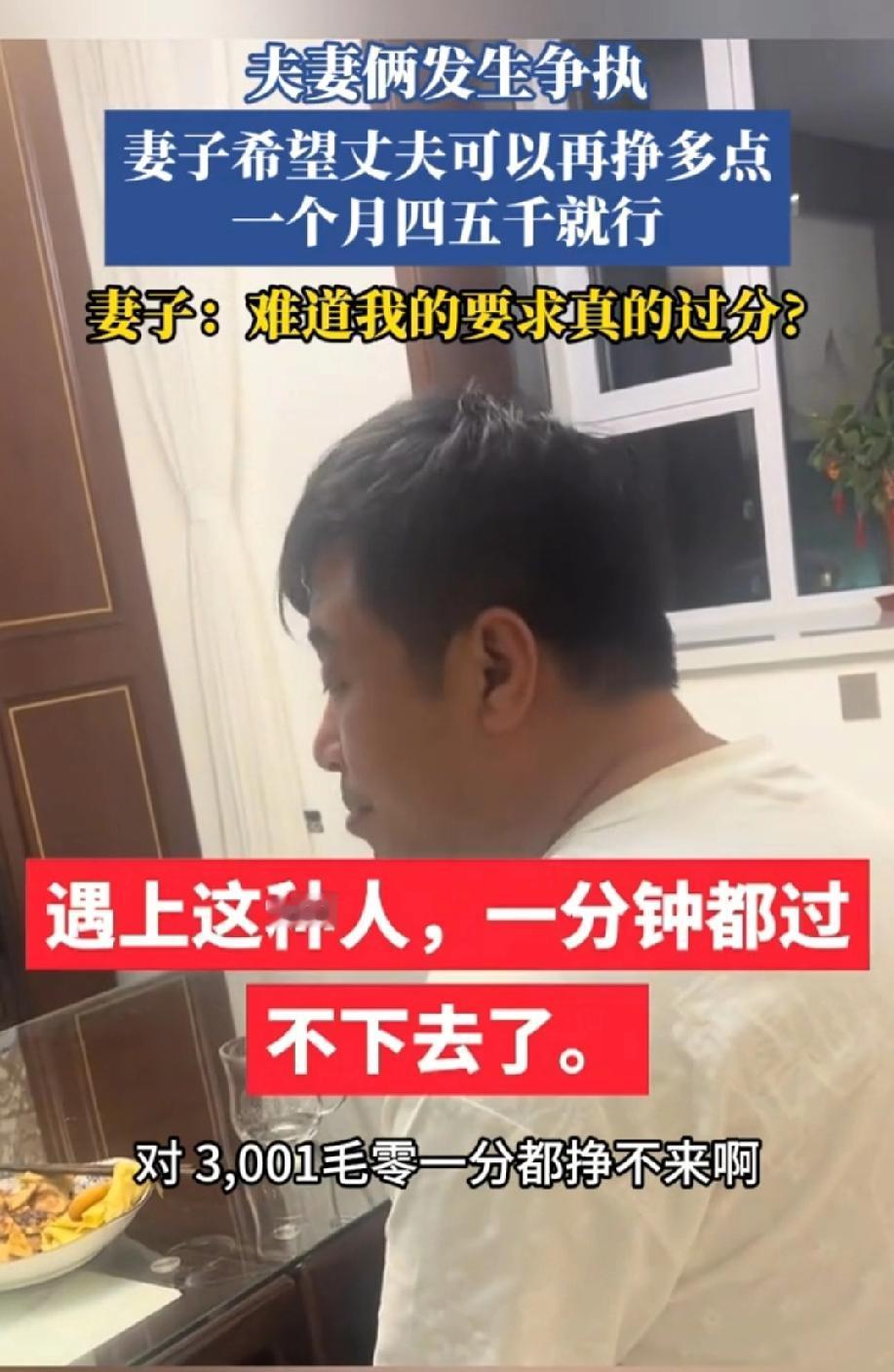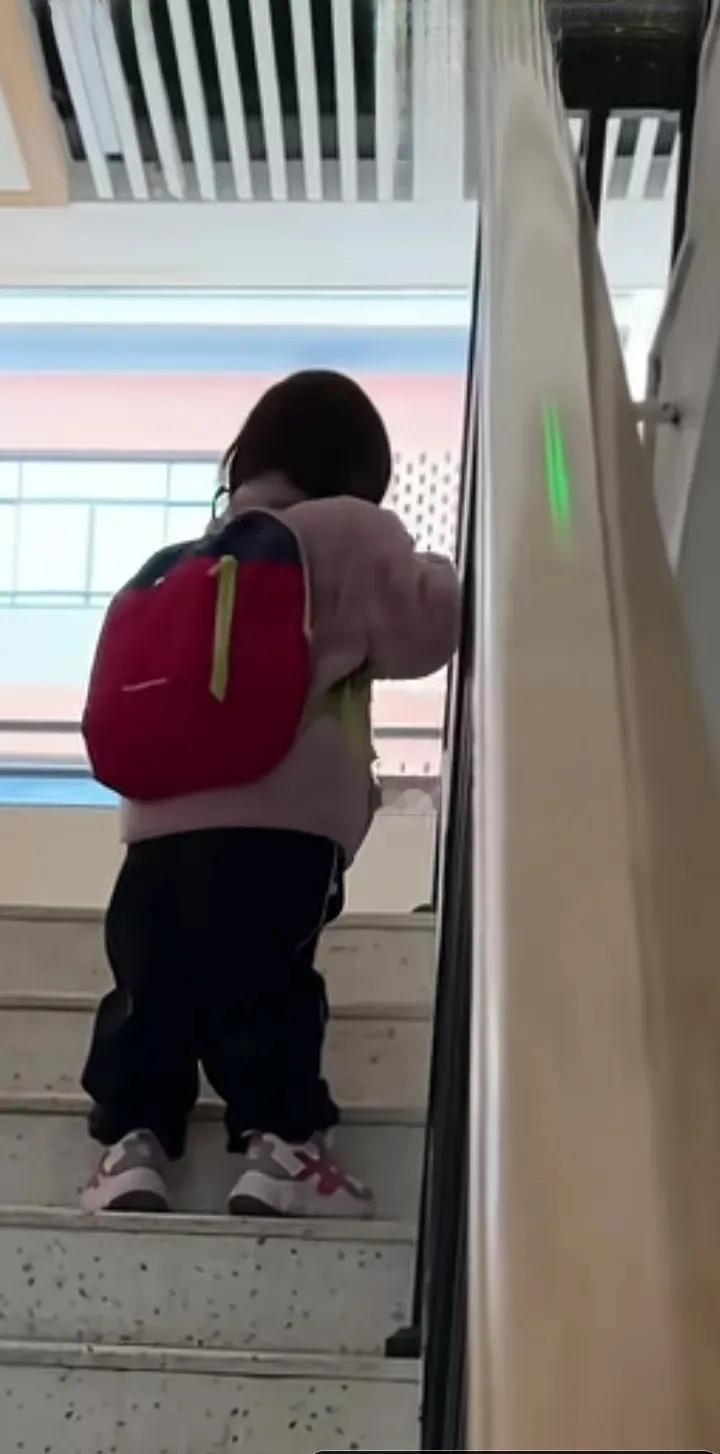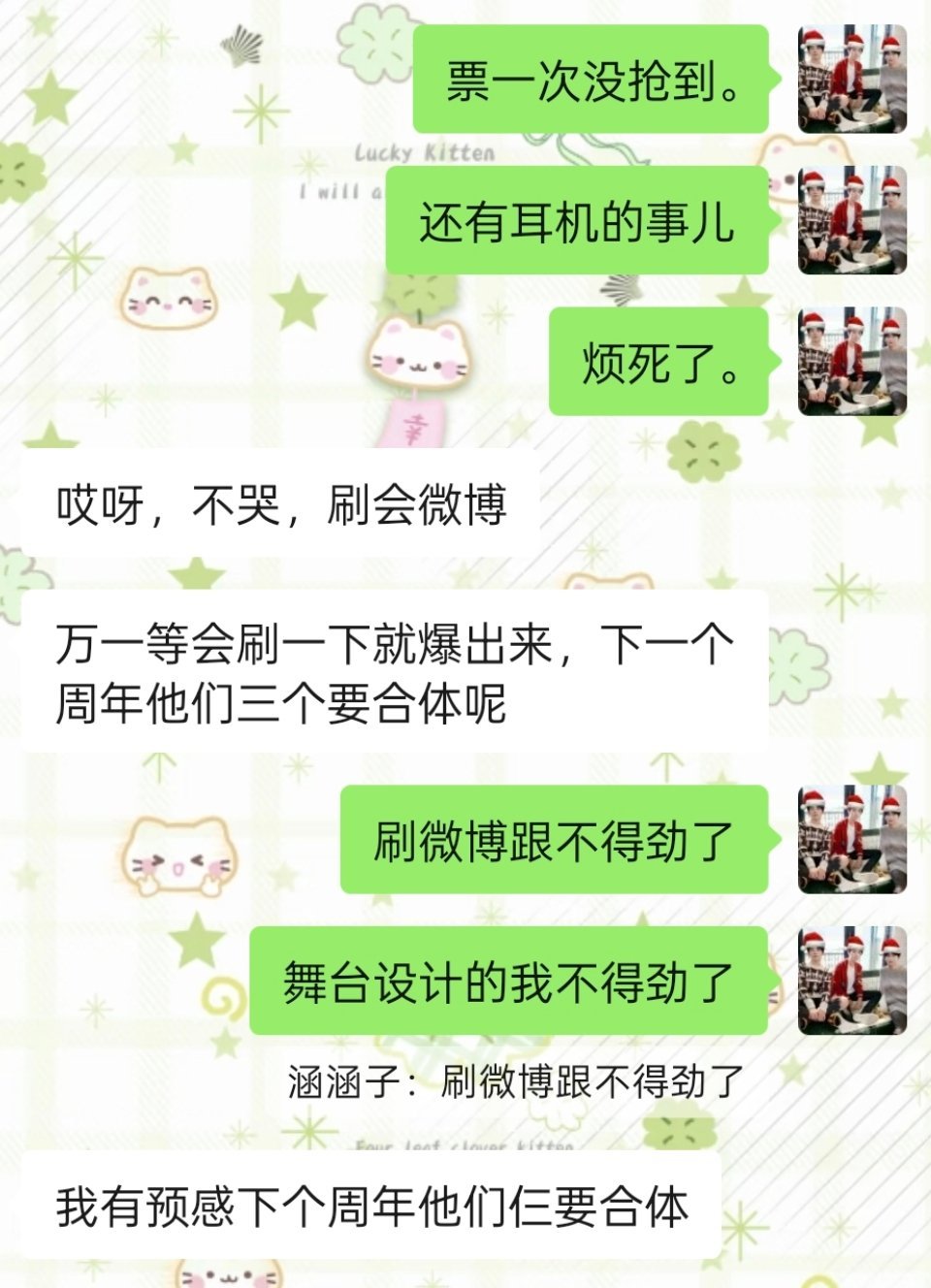1934年,新婚第二天,重感冒的苏青便撞见丈夫和表嫂在一起调 情。她忍了下来,连生5个孩子后,有一次苏青跟丈夫要生活费买米,哪知,丈夫一记耳光甩了过来:“你也是知识分子,你怎么不自己去赚钱。” 1934年的宁波,梅雨季的雨下得黏糊糊的。我裹着棉被坐在婚床上,重感冒让脑袋昏沉沉的,鼻尖总堵着,呼吸都带着铁锈味。昨天的红烛泪还凝在烛台上,像没干的血。 听见外屋传来表嫂的笑,银铃似的,裹着水汽钻进窗缝。我披了件夹袄下床,脚刚沾地,就看见堂屋门槛边,丈夫李钦明正扶着表嫂的腰,替她掸去旗袍下摆的泥点。表嫂的手在他胳膊上轻轻拍了下,嗔怪着什么,他的笑落在她发顶,暖得刺眼。 我扶着门框站了会儿,冷风从领口灌进来,咳嗽止不住地涌上来。他们猛地回头,表嫂的脸腾地红了,李钦明却只皱了皱眉:“你怎么起来了?病还没好。” “找水喝。”我转身回房,没看他。红盖头被我压在枕下,丝绸的滑腻蹭着脸颊,像谁在无声地笑。 这一忍,就是五年。 从宁波搬到上海,我在弄堂的小屋里生了五个孩子,大的牵着小的,小的抱着我的腿,哭声能掀翻屋顶。李钦明在洋行做事,回来越来越晚,身上的香水味换了一茬又一茬。我把《浮生六记》藏在尿布堆里,趁孩子睡了读两页,沈复写芸娘“拔钗沽酒,不动声色”,我摸着头上那支母亲给的银钗,指尖发颤。 那天米缸见了底,小女儿饿得直哭,嗓子都哑了。我拦着刚进门的李钦明,声音比蚊子还轻:“给点钱,买米。” 他脱大衣的手顿了顿,突然扬手一巴掌甩在我脸上。“啪”的一声,五个孩子都吓傻了,哭声戛然而止。 “你也是知识分子,”他的唾沫星子溅在我脸上,“读过书的,不会自己去赚钱?” 脸颊火辣辣地烧,可心里那点什么东西,像是被这巴掌打醒了。我想起十五岁那年,父亲还没破产,把我写的《我的理想》贴在客厅墙上,毛笔字歪歪扭扭,却写着“要做能自己挣钱的女人”。那时家里的书房堆着线装书,阳光透过雕花窗棂,在《漱玉词》上投下光斑,我以为日子会一直那样过下去。 可父亲的银行倒了,红漆大门被贴上封条那天,母亲把我的书捆了半麻袋,说“女孩子家,嫁个好人家才是正途”。我穿着嫁衣上花轿时,怀里还揣着本抄诗的册子,纸都磨软了。 那天晚上,我抱着哭累的小女儿,在油灯下写东西。笔是孩子用过的铅笔头,纸是烟盒拆开的硬纸壳,写的是弄堂里的油烟气,是孩子的哭声,是李钦明甩过来的那记耳光。写着写着,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一片蓝黑。 后来我把稿子寄给《宇宙风》,编辑沈从文先生回信说:“你的文字像宁波的咸风,带着股子韧劲。”拿到第一笔稿费那天,我去买了两斤米,还给每个孩子买了块麦芽糖。他们舔着糖笑,我看着他们的脸,突然觉得,那记耳光没白挨。 李钦明再要跟我分床睡时,我把写好的离婚协议推给他。他瞪着眼:“你离了我,怎么活?” 我指了指桌上的稿子,还有孩子们手里快吃完的麦芽糖:“靠这个,靠自己。” 走出弄堂那天,阳光正好。我牵着大的,抱着小的,手里攥着刚领到的稿费。风里飘着油条的香味,孩子们的笑声脆生生的。我想起爷爷书房里那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原来日子这门学问,要自己摔过、痛过,才能真的读懂。 后来有人说我写的东西“太俗”,净是柴米油盐。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些俗事,才让我在民国的风雨里,站直了身子,没被生活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