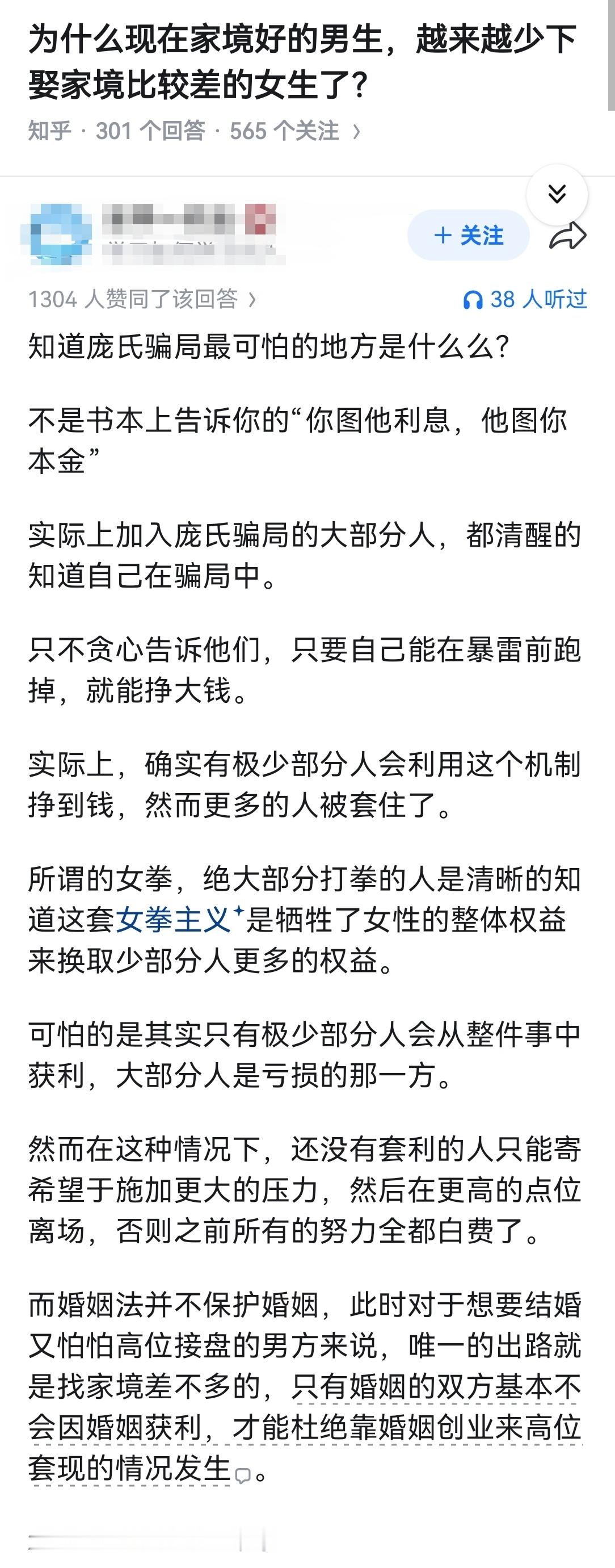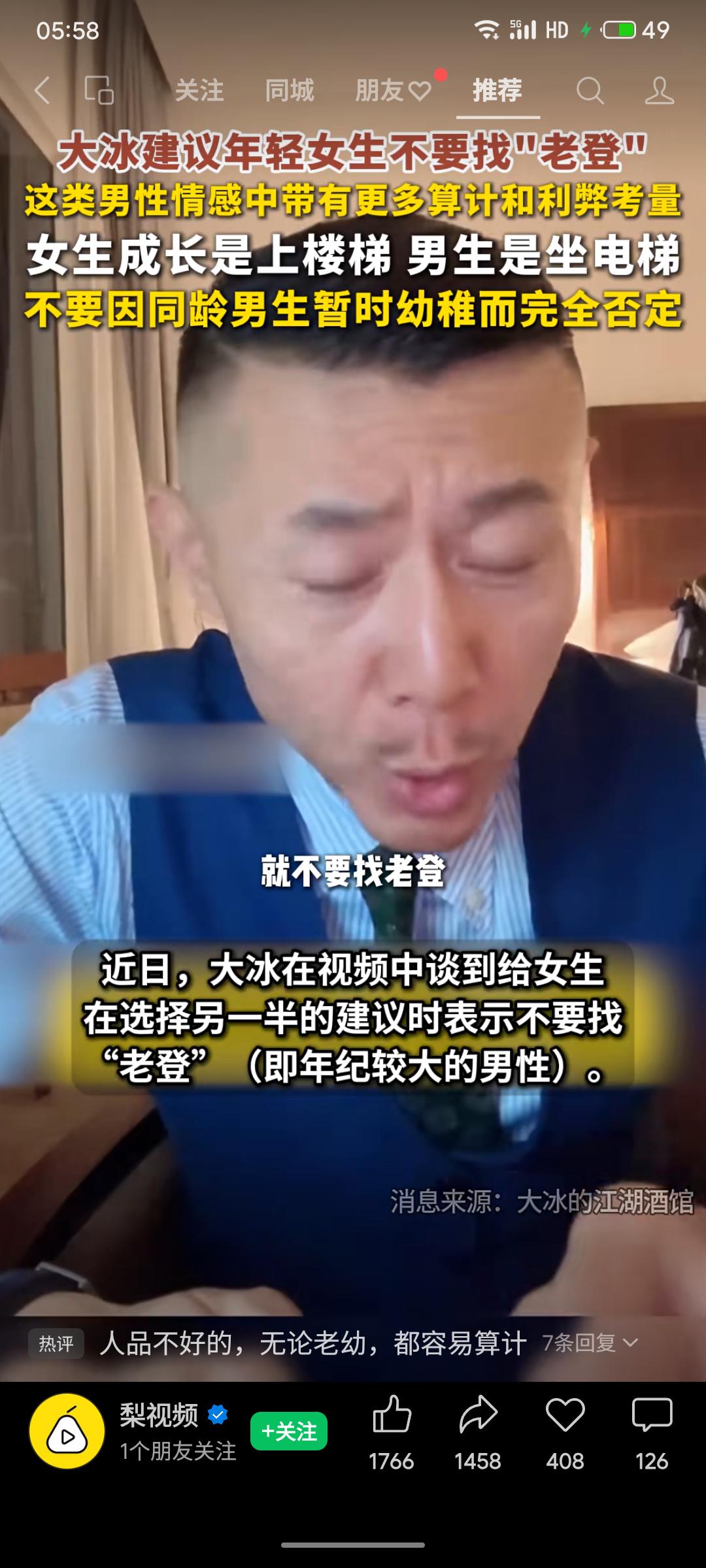1943年,郭婉莹难产住进医院,此时她的丈夫却留宿其他女人家。她不哭不闹,画好精致妆容,直奔他们私会的地方。敲开门后,郭婉莹微笑着,只说了4个字,丈夫二话不说跟她回家了。 1943年,那个名叫艾尔伯德的富商之子,在那个物资还未泛滥的年代,掏出一双足以羡煞旁人的美国玻璃丝袜,得意洋洋地炫耀它的“结实”,甚至许诺这双袜子能穿一年都不坏。 这一瞬间,对于从小看惯了稀奇货、甚至在中央造币厂厂长父亲膝下学过怎么养花的郭婉莹来说,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冒犯,她并不需要一双穿不烂的袜子,更不想嫁给一个眼中只有“实用”而无半分生活意趣的男人,这不仅是无趣,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贫瘠。 所以当艾尔伯德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被退婚,甚至甚至恼羞成怒提着枪找上门来时,十九岁的郭婉莹展现出了极其罕见的逻辑闭环和镇定,面对指着脑门的枪口,她没有惊声尖叫,反而冷静地抛出了两条让对方瞬间泄气的真理:要么杀了她,这婚结不成。 要么杀了他自己,连命都没了,婚更结不成,这场闹剧,最终在艾尔伯德的自我挫败中收场,但也彻底显露了郭婉莹骨子里那种像剔透水晶般坚硬的质地,她宁愿要带刺的玫瑰,也不要一株只能当摆设的塑料花。 后来在燕京大学,她果然选择了一条世俗眼中“不划算”的路,那个叫吴毓骧的男人出现了,身为林则徐的后代,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美,既有麻省理工的学历,又有那种能把生活过出花来的浪漫。 尽管很多人觉得这是一次“下嫁”但在郭婉莹眼里,这个男人有趣,这比什么都重要,但生活往往就在你以为抓住了诗意时,狠狠给你一记耳光,婚后那个曾经风度翩翩的吴毓骧,露出了凡夫俗子的劣根性。 他开始流连牌桌,甚至在郭婉莹难产、女儿生病的危急关头,还留宿在一个年轻寡妇家中,换作任何一个普通的旧式女子,大概早就哭天抢地或是回娘家搬救兵了,但郭婉莹不一样,她的骄傲不允许她失态。 几天后,她没有蓬头垢面地去撕扯,而是坐在镜子前,细细地描眉画眼,穿上得体的衣裳,在一众朋友的陪伴下敲开了那扇门,她没有给任何人难堪,只是微笑着对那个不仅没了魂还在输钱的男人说了一句:“该回家了”。 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比一哭二闹更有雷霆万钧的力量,吴毓骧满面羞愧地跟了回去,而回到家后,郭婉莹把所有的屈辱和悲伤都独自咽下,绝口不提,日子照过,但这事之后,她清醒了,那种想做温室花朵的念头彻底断了,她开始和朋友合伙开服装店。 做起了哪怕只有短暂光景的女老板,如果说前半生的波折还是在那层锦绣帷幕里的小打小闹,那后半生的命运才是真的要把她按进尘埃里摩擦,1958年吴毓骧因故入狱,三年后在牢房里因病撒手人寰。 留下给郭婉莹的,除了一堆还不清的14万元债务,还有破碎的家庭和彻底被没收的家产,为了还债,她卖光了所有家底,曾经出入有小车接送的郭家四小姐,带着孩子挤进了一个只有7平米的小亭子间。 屋顶是破的,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早晨醒来时脸上常常结着一层冰霜,为了生存,甚至是为了赎那份不属于她的罪,她被送进了学习改造班,这双手,曾弹过钢琴,摸过最名贵的绸缎,如今却要抡起铁锤砸石块,提着沉重的水泥桶在工地上奔波。 甚至要去清理臭气熏天的厕所,要在深夜的鸭棚里枕着干草入睡,每天从那些肮脏繁重的劳动中直起腰,她的午餐往往只是一碗只有几分钱的阳春面,然而令人惊叹的是,在这个被所有人视为“炼狱”的过程中,没人听过郭婉莹一声抱怨。 英国记者后来不怀好意地采访她,想听听这位曾经的贵族如何控诉那段不堪的岁月,郭婉莹却把背挺得笔直,轻描淡写地回应说,那是为了保持体型,如果不那样劳动,她或许早就发胖了。 在那个漏风的亭子间里,当阳光穿过破洞射进来时,她告诉孩子们这一幕很美,在买不起烤箱的日子里,她能用铁丝网架在煤球炉上,给孩子烤出金黄焦脆的吐司,就算只能用铝锅蒸蛋糕,她也要做出圣彼得堡的风味。 这是父亲从小教给她的风骨,要有骄气,但不能有娇气,真正的贵族,不是看你此时此刻坐在多豪华的沙发上,而是看你即便跌进烂泥里,还能不能保持喝下午茶时的那种从容,甚至连她的儿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知道母亲究竟受过多少苦。 那些血泪都在母亲轻快的玩笑中消解了,直到1966年以后,她重回讲台教英文,面对周围同事的冷眼与排挤,她依然是一副昂着下巴、一丝不苟的模样,她从未想过离开中国,当被问及为何不随家人去海外避难,她的回答掷地有声:“我是中国人,这是我的家”。 1998年,89岁的郭婉莹走完了她跌宕起伏的一生,她把自己最后的躯体也捐献了出去,什么都没留,却又什么都留下了,挽联上写“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这不仅仅是对一位名媛的祭奠,更是对一种精神的注解。 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