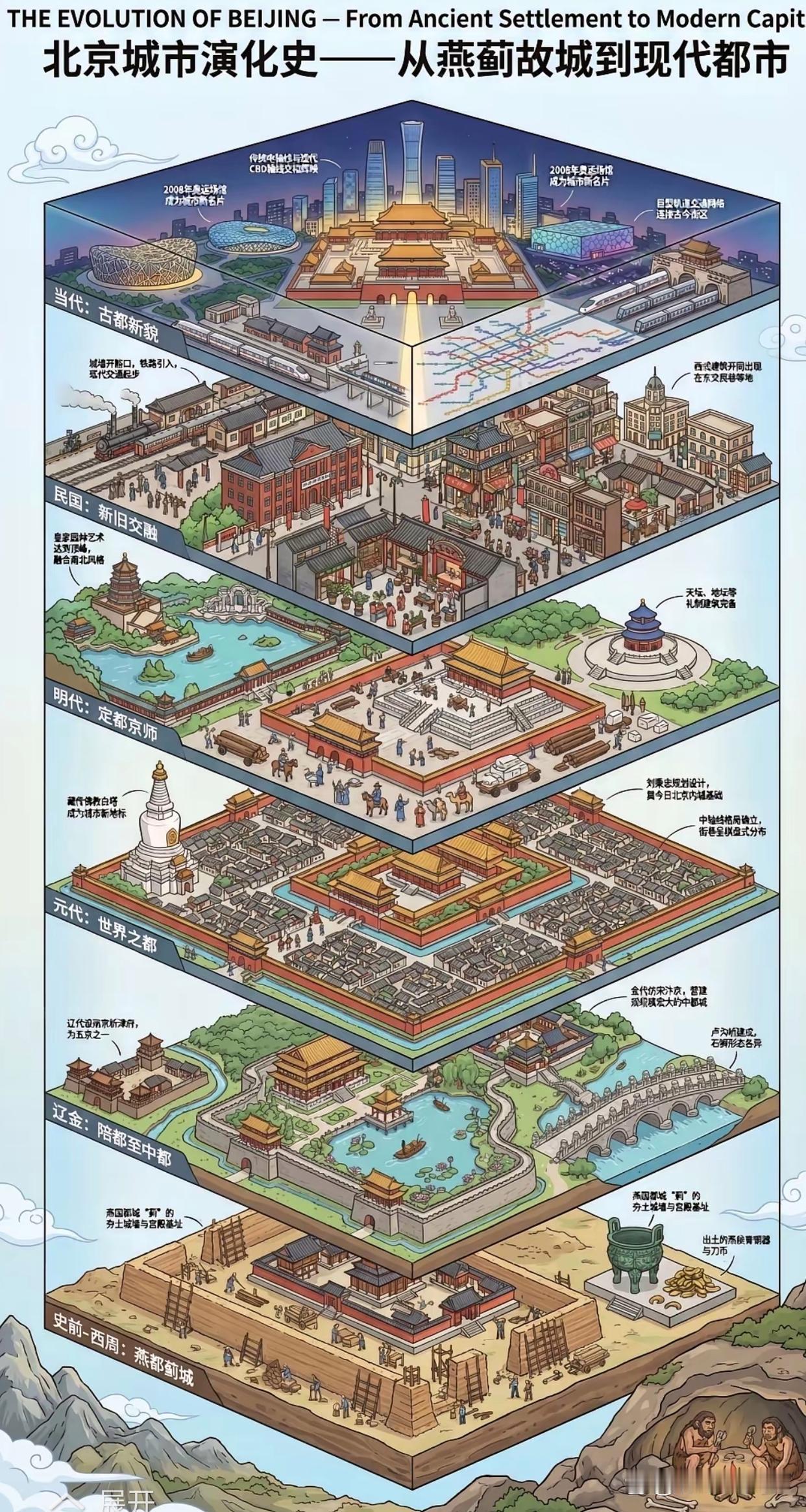乔同志与家人的合影。 1990年初夏,乔同志和夫人、子女在北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当时乔同志66岁,坐在中间的藤椅上,面带微笑,其他人分坐在两侧 一九九零年初夏,北京一处小院,藤椅摆在当中,乔石六十六岁,坐在椅子里,背轻轻一靠,嘴角带笑,夫人和子女分坐两侧。 这张合影,起初只是家里一张普通照片。 多年以后,讣告写明他于六月十四日七时零八分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消息一出,悼念刷满屏,照片被反复转发。很多人看着照片里温和的长者,脑子里蹦出来的却是民主、法治、宪法、人大这些字。 他的一生绕不开这几个词。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他出生在上海,少年时接触进步思想,参加抗日救亡。一九四零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同济大学地下党、上海新市区委、市北一区学委等组织里忙个不停,当过地下党总支部书记、副书记,是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 那会儿谈改变中国,多半还停留在传单和油印小册子上,制度距离日常生活很远。 解放前后,组织让他在青年和工业两个战线之间穿梭。 杭州市委青年部门、华东局青年统战、鞍钢和酒钢等单位的工程技术处、设计院、研究院,他都待过。看似绕路,实际上把青年工作、企业管理、工业建设都摸熟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他调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期同外国政党、外国政府打交道,更清楚什么叫“按规矩办事”。 “文化大革命”掀翻了很多规矩,他也被卷进去。后来他一再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语气不高,却透出那几年留下的硬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重回中枢。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先后任中联部副部长、部长。一九八二年九月当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九八三年兼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着手让中办从运动式状态回到按章程办事。一九八四年,他兼任中组部部长,推动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尽量做到人岗相配。 一九八五年,他接管政法工作,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同年九月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九八六年又兼任国务院副总理。 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这些系统,都归他分管。他对法院的要求很直接:办案最重要是依法,关键时候该顶住要顶住,不顶住,那还要法院干什么。 对检察机关,他强调党主要管方向、管政策,要帮他们挡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干扰。 对律师,他明确提出要保护律师依法执业,对阻挠、打击要坚决处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一步步纳入制度和法律轨道。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他公开支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认定市场经济离不开法律这把尺子。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他兼任宪法修改小组组长。 一九九三年三月,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八届人大任期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一百二十九件,通过八十五部法律和三十三个决定,共一百一十八件,还批准了六十个双边或多边条约、公约和重要协定。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担保法、票据法、保险法、价格法,以及预算法、人民银行法等基础性法律,都在这一时期出台,市场经济总算有了一整套成形的“游戏规则”。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四日,修宪过程中出现过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中共中央同意宪法修改小组的报告,并提出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来不及再开会,大会主席团按宪法又不能直接提出补充草案,有人觉得代表讨论时普遍同意,算是走完程序。 他听完心里没底,召集会议请法律专家拿主意。 王汉斌提出,应按宪法由五分之一以上全国人大代表联合签名提出补充草案。 他当场点头,说就按这个办,没想到“五分之一代表签名”,是自己考虑不周,责任由他来担。 大会常务主席会议采纳这一意见,三十二个代表团的两千三百八十三名代表联合签名,补上了程序上的漏洞。那次修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写进宪法,也把改革开放成果固定在根本大法中。 闭幕时,他讲得很明白:依法治国是国家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一年后,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九九九年修宪,这句话正式写入宪法,从“法制”到“法治”,他一路推着往前挪。 对人大工作的地位,他也说得不绕弯。 有次同各省区市人大负责人座谈,他提醒,宪法和法律已经把人大的地位讲清楚了,有些人还把人大当成“退居二线”的地方,这种想法得改。如果自己都觉得人大没事干,那工作肯定搞不好。 一九九四年在贵州考察时,他说,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如果自己不把法律当回事,还怎么让老百姓守法。 在他看来,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扣在一起的,法律既是底线,也是护栏。 改革开放多年走到今天,民主和法治仍是公众绕不开的话题,人们在网络上悼念他,说到最后,总要扯到规则、公正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