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和母亲走,是两回事。 我爸走那年,家里顶梁柱塌了。但过年,年夜饭的桌子照样摆得满满当当。 我妈一个电话打过来,声音还是那么响:“都回来,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兄弟姐妹,还是会从天南地北赶回去,挤在一个屋里。只是吃饭的时候,主位上那个空着的凳子,谁也不敢去看。 我妈那时候已经七十多了,背有点驼,却硬撑着把家里的事扛了下来。父亲走后的第一个冬天,她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备年货,腌腊肉、灌香肠,窗台晾满了咸鱼干,都是我们小时候爱吃的味道。 我劝她别累着,找个超市买点现成的就行,她却瞪我一眼:“现成的哪有家里的味儿?你们回来,就得吃妈做的。” 她记性不如以前,却把每个孩子的喜好记得清清楚楚:大哥爱吃甜口的糯米丸子,二姐不吃香菜,我偏爱的糖醋排骨要多放冰糖,就连孙辈的过敏食材,她都写在小本子上,贴在厨房墙上。 年夜饭开席前,她会把父亲的酒杯摆上,倒半杯他生前爱喝的米酒,轻声说:“老头子,孩子们都回来了,你也尝尝。” 然后才招呼我们入座,自己坐在父亲旁边的位置,不停地给我们夹菜,嘴里念叨着“多吃点”“工作别太累”,仿佛只要她还在张罗,这个家就还是完整的。 饭后我们围在客厅聊天,她坐在沙发中间,听着孩子们打闹,嘴角一直带着笑,可我分明看见她趁我们不注意,用袖口擦了擦眼角——那是想念父亲,却怕扫了我们兴致的隐忍。 真正的崩塌,是母亲走后。 她走在一个深秋的清晨,走得很安详。可从殡仪馆回来的那天,推开老房子的门,一股冷清扑面而来。 窗台的咸鱼干早就没了,厨房的小本子还贴在墙上,字迹已经有些模糊,腌菜坛子空了,灶台上落了薄薄一层灰。 大哥叹了口气,拿起抹布想擦擦,却愣在原地,最后只是放下了——他知道,再怎么擦,也擦不出母亲在时的烟火气了。 那年过年,没人再打那个催我们回家的电话。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在家族群里问了句“今年回家过年吗”,半天没人回应。 过了好一会儿,二姐回:“孩子要上补习班,就不回了,你们聚吧。”三哥跟着说:“工地年底忙,走不开。”最小的妹妹说:“太远了,来回折腾,明年再说。”最后,只有我和大哥回了老家。 年夜饭是在外面餐馆订的,两荤两素,摆在空荡荡的餐桌上,显得格外冷清。没有了母亲提前半个月的忙碌,没有了满屋子的香气,没有了她念叨的家常话,就连父亲的那个空凳子,我们都忘了摆。 吃饭的时候,大哥喝了口酒,突然说:“以前妈在,再忙也得回来,现在……回来干啥呢?”一句话,让我鼻子发酸。是啊,母亲不在了,那个让我们跨越千里也要奔赴的“家”,好像就没了牵挂的锚点。 我翻出母亲留下的旧毛衣,那是她给我织的,袖口磨破了,她又用同色的线补了一圈,针脚有些歪歪扭扭,却是她一针一线熬了好几个晚上的成果。以前总嫌样式老气,压在衣柜最底层,现在拿在手里,却觉得沉甸甸的。 还有她腌萝卜干的坛子,我洗干净了,试着按她以前的方法做,可盐放多了,又咸又涩,怎么也做不出她那个酸甜脆爽的味道。原来,母亲的味道,是独一份的,没人能替代。 第二年清明,我们兄弟姐妹终于凑齐了,一起去给父母上坟。烧纸的时候,小妹突然哭了:“我好想妈,想她做的红烧肉,想她骂我懒虫,想她冬天给我暖脚。”二姐也红了眼:“早知道妈走得这么快,去年过年说啥也该回来。”大哥拍了拍我们的肩膀,没说话,可我看见他的眼眶也红了。 我们都明白,父亲走,是失去了支撑家的力量;母亲走,是失去了维系家的温度。父亲在,家有骨架;母亲在,家有血肉,两者都在,才是完整的家。 后来,我们也偶尔聚聚,却再也没回老房子过年。要么在大哥家,要么在小妹家,饭菜是现成的,聊天是客气的,再也没有了以前挤在老屋里、吵吵闹闹却满心欢喜的感觉。 我才慢慢懂得,母亲不是家里的“配角”,她是那个把散落的兄弟姐妹串联起来的线,是那个让家有烟火气、有归属感的根。父亲走了,根还在,家还能勉强支撑;母亲走了,根断了,家就成了一盘散沙。 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父母在时,总觉得时间还长,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忽略了他们的等待;父母走后,才发现,那些曾经嫌弃的唠叨、厌烦的牵挂,都是再也找不回的幸福。 父亲走,是顶梁柱塌了,我们还能互相扶持;母亲走,是灵魂没了,我们只能在回忆里寻找家的模样。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别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趁他们还在,多回家看看,多听听他们的唠叨,多尝尝他们做的饭菜——那才是世间最珍贵的温暖。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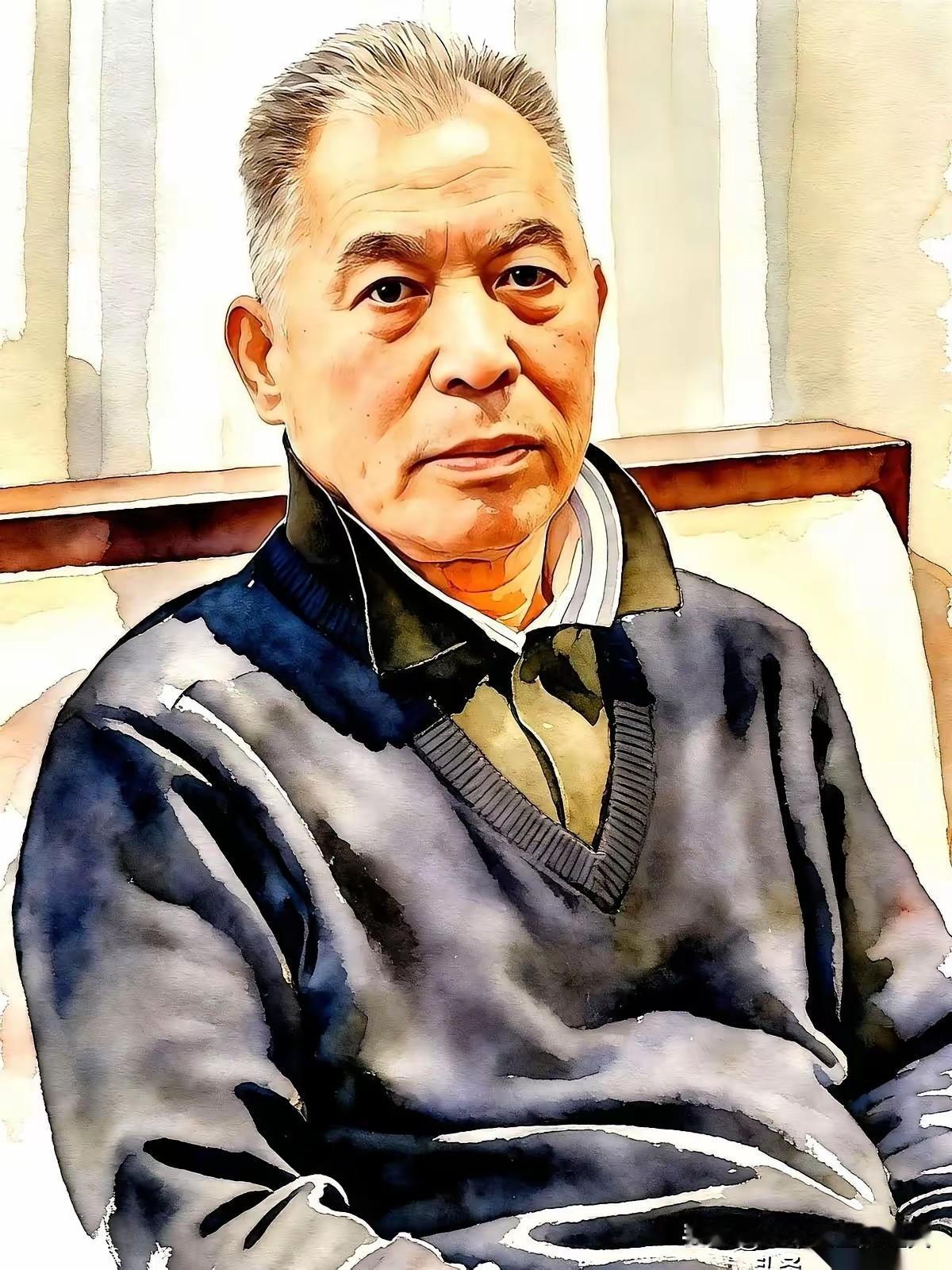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