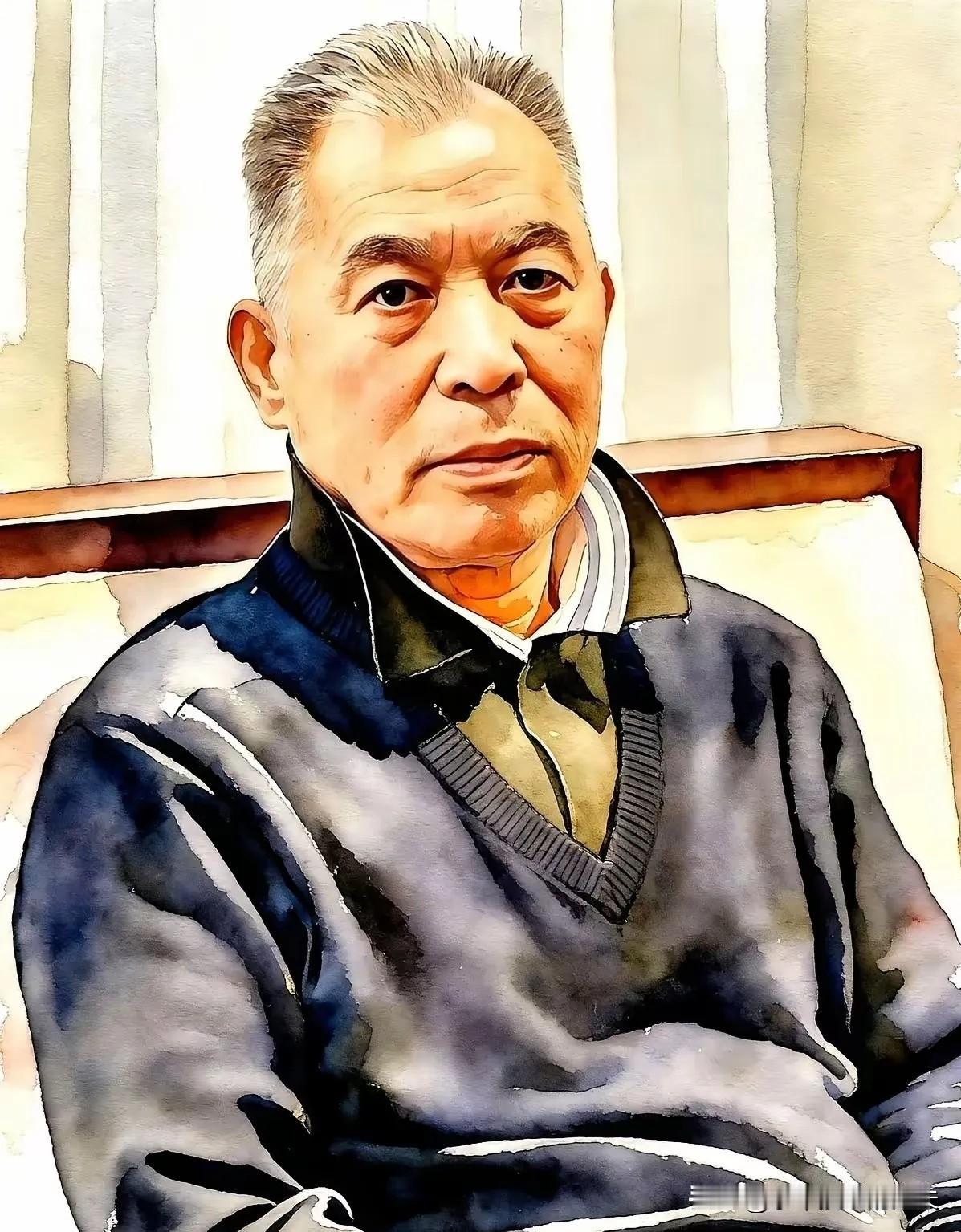父亲走,和母亲走,是两回事。 我爸走那年,家里顶梁柱塌了。但过年,年夜饭的桌子照样摆得满满当当。 那年我28岁,刚成家没两年,还没学会扛起一个家的重量。父亲突发心梗走得突然,出殡那天雪下得没膝盖,母亲跪在灵前,眼泪冻在脸上,却没哭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嚎啕。 我以为她会垮,可头七刚过,她就踩着凳子够橱柜最上层的蒸笼,说“还有仨月就过年了,你爸爱吃的糯米丸子,得提前练手”。 母亲一辈子没上过班,围着灶台和家人转了四十多年。父亲是厂里的技术员,话少,工资全交家,家里大小事都是母亲拿主意,可谁都知道,父亲是母亲的主心骨,母亲是这个家的魂。 父亲走后,母亲的腰好像更弯了,却把家里的节奏掐得更紧:腊月初八腌腊肉,腊月二十蒸馒头,年三十下午就开始在厨房忙活,煎炒烹炸的声音,盖过了家里偶尔的沉默。 那年年夜饭,桌子确实摆满了。父亲爱吃的红烧肉炖鹌鹑蛋、糯米丸子、炸藕夹,一样没少,甚至比往年还多了两道菜。 母亲把父亲的碗筷摆在他常坐的位置,倒了小半碗他爱喝的二锅头,轻声说“老陈,尝尝今年的丸子,我多放了点荸荠”。我和姐姐、弟弟都不敢说话,低头扒饭,眼泪掉在碗里,咸得发苦。 母亲却像往常一样,给我们夹菜,说“多吃点,明年都得好好的”,她自己筷子没动几口,眼睛却一直盯着父亲的空碗筷,直到菜凉了,才默默把那碗酒泼在门口的雪地里。 那些年,母亲就靠着这股“撑着”的劲儿,把家黏在一起。每年过年,她都坚持做一桌子父亲爱吃的菜,摆上他的碗筷,仿佛他只是出了趟远门,随时会推门进来。 我知道,她是怕这桌子一冷,这个家就真的散了。有次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母亲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对着父亲的照片发呆,手里攥着父亲生前穿的旧棉袄,棉袄的袖口,还留着母亲缝了又缝的针脚。 这样的年夜饭,母亲撑了十二年。直到她72岁那年,查出胃癌晚期。住院期间,她还念叨着“快过年了,糯米粉还没买”,我们忍着眼泪说“您放心,今年我们来做”,母亲摇摇头,说“你们做的,不是你爸爱吃的味儿”。她走在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距离过年还有七天。 母亲走后的第一个年,我学着她的样子准备年夜饭。照着她留下的笔记,腌腊肉、蒸馒头,可红烧肉炖糊了,糯米丸子散了架,炸藕夹吸满了油,难以下咽。 桌子没摆满,父亲的碗筷还在,却没人再敢像母亲那样,轻声跟他说句话。姐姐哭着说“妈不在,这年没法过了”,弟弟低着头,把没喝完的酒倒在地上,说“爸,妈来陪你了”。 那一晚,菜没怎么吃,灯亮到天明,没人说话,只有偶尔的抽泣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荡。 我才真正明白,父亲走,是顶梁柱塌了,可母亲还在,家的框架还在,烟火气还在;母亲走,是家的魂没了,再满的桌子,也填不满心里的空。 父亲在时,母亲有依赖,我们有靠山;母亲在时,无论遇到什么事,只要回到家,闻到厨房的香味,就觉得踏实。 母亲走了,才发现那些年的年夜饭,摆的不是菜,是母亲的牵挂,是她想留住这个家的执念。 后来,每年过年,我们姐弟仨还是会凑在一起吃年夜饭。学着母亲的做法,慢慢摸索,味道渐渐有了几分相似,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直到今年,我女儿突然说“奶奶做的丸子,是不是会放糖呀”,我才想起,母亲做糯米丸子时,会偷偷放一点白糖提鲜,这是她没写在笔记里的秘密,是只属于我们家的味道。 父亲走,是失去了支撑;母亲走,是失去了归宿。一个家,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地都在,才有家的模样。 那些年母亲撑起来的年夜饭,不是为了摆满桌子,是为了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家人在,家就在,日子就得好好过。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