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到一段1963年的旧事,真是一身冷汗。 那时候教员就痛批文艺界,说他们不演工农兵,整天搞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甚至成了“外国死人部”。 1963年的北京,长安大戏院的霓虹灯亮得晃眼,门口的海报贴满了《长生殿》《桃花扇》这类古装戏,买票的队伍排到了胡同口。离戏院不远的工厂宿舍区里,老工人王德福揣着皱巴巴的戏票,却在海报前叹了口气。他原本盼着能看一场讲炼钢工人的戏,结果满眼都是蟒袍玉带、才子佳人的卿卿我我,转身就把票送给了邻居。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全国各大城市都在上演,舞台上的故事离工厂的高炉、农村的田埂越来越远。 当时的文艺界,正陷入一场集体性的“怀旧潮”。北京人艺排演的《蔡文姬》,耗资数万置办行头,曹操的铠甲用的是真皮革,蔡文姬的衣裙绣满金线,一场戏的成本够普通人家过好几年。郭沫若的历史剧一部接一部,从《屈原》到《武则天》,帝王将相的雄才大略、爱恨情仇被反复演绎。地方剧团更是跟风,陕西的秦腔团放下了《梁秋燕》这样的现代戏,转头排演《三滴血》;河南的豫剧团停了《朝阳沟》的巡演,改演《穆桂英挂帅》。有人统计过,1963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剧团里,演现代戏的不足三成,剩下的七成,全在啃老祖宗的剧本。 “才子佳人”的戏码更成了香饽饽。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的《桃花扇》,光是女主角的戏服就做了二十多套,镜头里满是亭台楼阁、诗词歌赋,却没一句台词提到底层百姓的疾苦。作家们的笔也跟着转向,要么写古代文人的风流韵事,要么写民国知识分子的爱恨纠葛,很少有人愿意走进农村,去写合作社里的争分夺秒,去写农民脸上的汗水。有位青年作家试着写了一篇关于拖拉机手的小说,投稿后却被编辑部退回,理由是“缺乏艺术性,太接地气”。 “外国死人部”的帽子,更是精准戳中了崇洋媚外的痛点。当时的出版社扎堆翻译外国古典文学,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集摆满了书店的橱窗,本土作家的新作却被挤到了角落。文艺界的座谈会上,专家们言必称“莎士比亚的戏剧结构”“托尔斯泰的叙事手法”,却对《白毛女》《小二黑结婚》这样的本土作品不屑一顾。有个话剧团排演外国剧目,连演员的台词都要刻意模仿翻译腔,引得观众吐槽“听着像嘴里含着石头”。 这样的乱象,早就背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定下的方向。1942年,教员就明确说过,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扎根人民群众。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界确实出过不少好作品,《白毛女》让观众跟着哭,《李双双》让农民跟着笑,那些贴着泥土气息的故事,才是老百姓真正想看的。可到了1963年,十五年的时间过去,有些文艺工作者忘了本,住进了城里的洋房,坐上了小汽车,再也不愿迈开腿走进田间地头。他们觉得工农兵的故事“土”,觉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雅”,却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 教员的批评,不是凭空发火,而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会议上拿着文艺界的工作报告,拍着桌子说:“你们写的东西,工人看不懂,农民听不懂,给谁看?给帝王将相看?给才子佳人看?”这话传到基层文艺工作者耳朵里,有人羞愧,有人警醒。河北的一个县剧团,当场就把排了一半的古装戏停了,演员们扛着铺盖卷住进了农村,跟着农民一起下地、一起开会,三个月后排出了《夺印》,演的是农村干部和坏分子的斗争,巡演时场场爆满,台下的观众跟着喊口号,掌声能掀翻戏台。 这场批评之后,文艺界确实迎来了一阵新风。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作品横空出世,李玉和的铁路工人形象、阿庆嫂的茶馆老板娘形象,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这些戏里没有帝王将相,没有才子佳人,只有普通人的英雄气概,只有工农兵的家国情怀。可遗憾的是,后来的发展逐渐走向极端,不少优秀的传统剧目被一刀切地禁演,一些文艺工作者也遭到了不公对待,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历史的教训值得铭记,文艺从来不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而是要扎根大地、扎根人民。那些脱离群众的作品,终究会被时代遗忘;那些贴着人心的故事,才能永远流传。文艺工作者只有真正走进工农兵的生活,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这是1963年那段旧事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示。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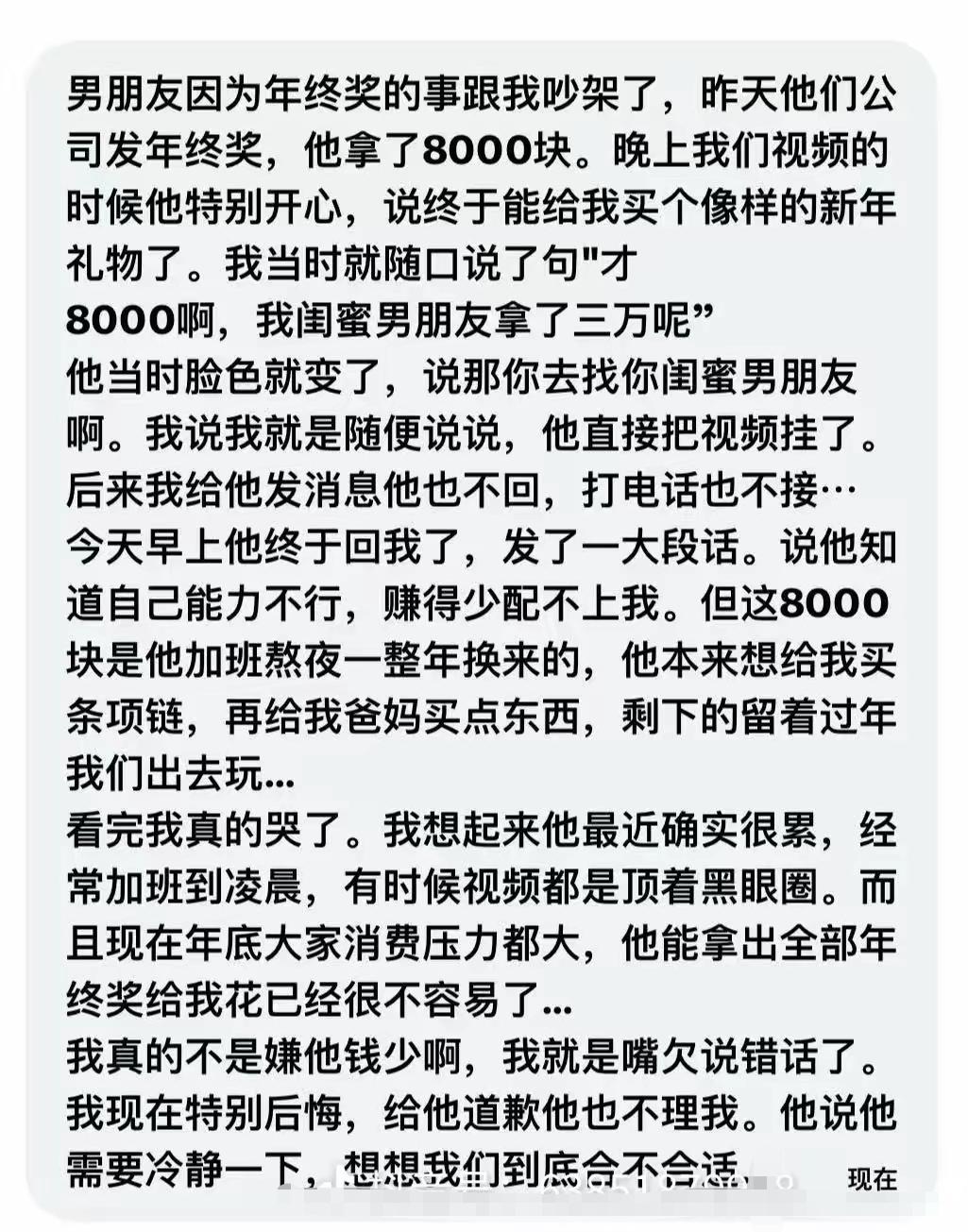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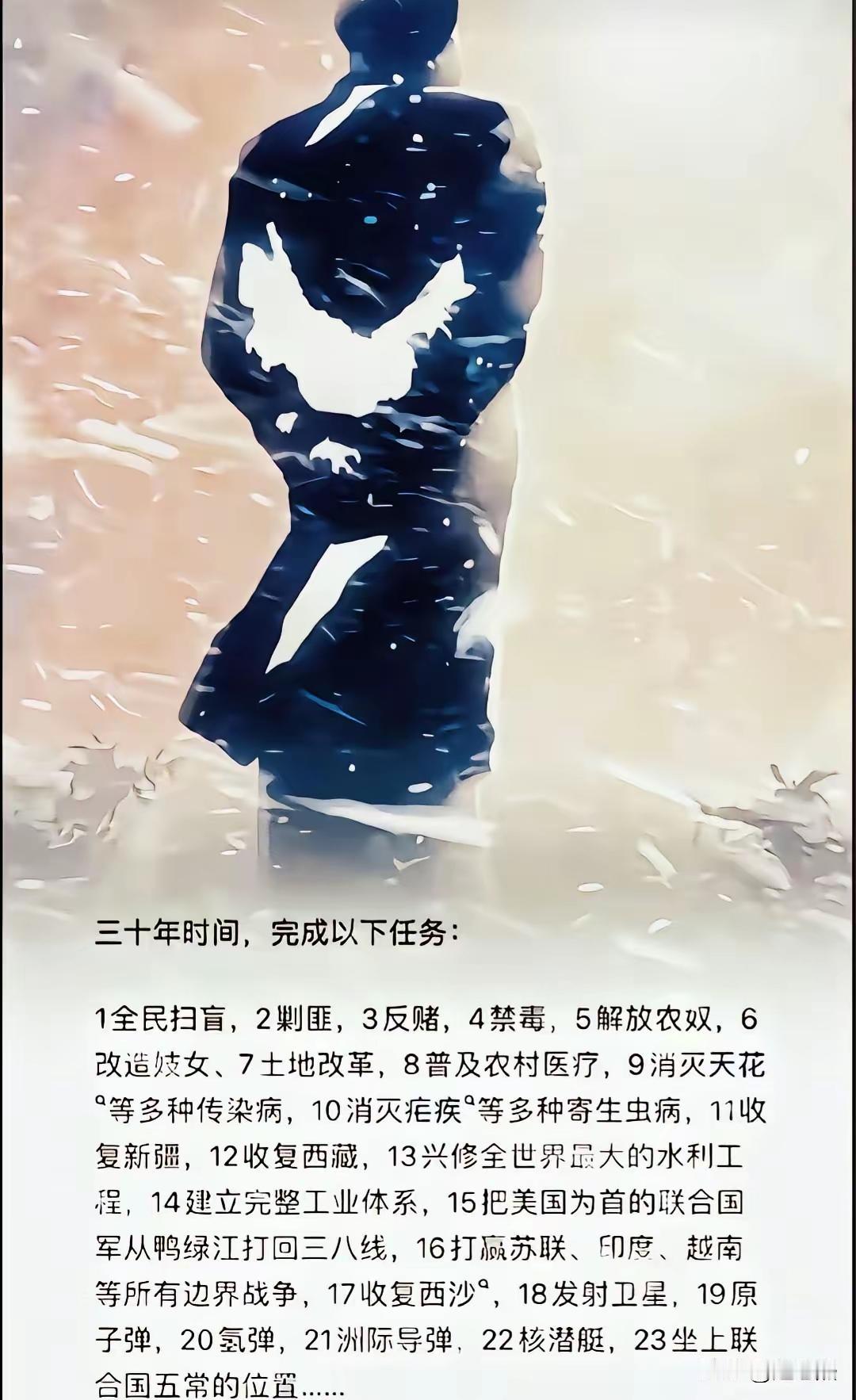


![形象!太形象了![捂脸哭][捂脸哭][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3584259342957093181.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