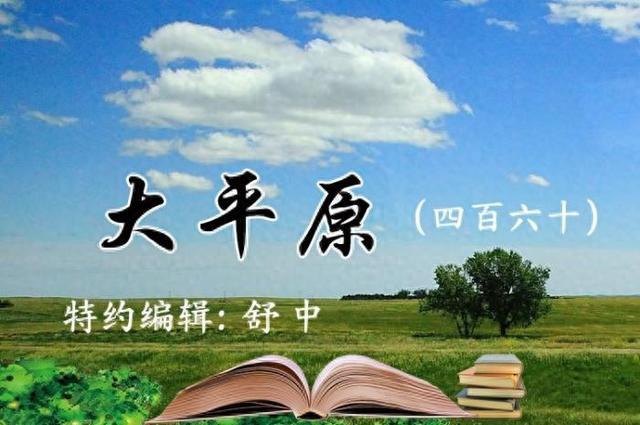
洗手洗脸的过往
文/耿兴义
过去,我们乡下人的日子过得着实穷困拮据,那没吃少穿就甭说了,甚至连块正儿八经的洗手擦脸的手巾都没有。
记得那时家家户户的住房,因常年累月的烧水做饭,屋门被烟火熏得黑呼呼、脏兮兮。可就在这古拙、粗糙、黑呼呼、脏兮兮的木门上,锈迹斑斑的门环却常年吊着一块像门幡一样的土纺土织或白或花带有穗头的老粗布。这就是一家人共用的手巾,家乡人惯叫它机裙子。之所以把它吊在一进门醒目的当眼处,就是为全家人使用起来,随手、方便。
那时经年累月拿着身子当地种的大娘婶子们,一到冬天,难得农活的闲暇,她们便把心思又转到操持一家老小的冬棉夏单上。没白没黑的纺啊,络啊,织啊,缝啊,做啊,那挂在门上的老粗布,就是一机布织下来,从布的末端连同剩在机上不能再织的经线一块剪下来的布尾巴,布头子。为了好看,人们又把布头上那根根散落耷拉着的经线捋股辫成穗头。
俗话说富日子讲究,穷日子将就。在那个年代,乡亲们过日子靠的就是吃苦耐劳,省吃俭用这一老本份。什么都是得过且过,凑凑合合,将将就就,没有一点奢望,只要过得去就行。老粗布头子做手巾,还不是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
吊在门环上方便全家人洗手擦脸的机裙子对小时候的我却很不“感冒”。大多孩子小时候都不爱洗手擦脸,不是让大人呛着、就是哄着。何况那时洗手洗脸后,手上脸上的水沥沥拉拉,还要凑到屋门根前。我们个子又矮,只能颠起脚、举着手,昂脖仰脸使劲向上夠才能擦着,费劲不说,这一来手上脸上的水顺势流进袖管和脖领子里,弄得湿漉漉的很不舒服,尤其大冬天,凉呱呱的,有时还会结冰哩,那个难受劲啊。不仅如此,那土纺土织的机裙子,布面粗糙的像麻袋片一样,格格楞楞,拉里拉碴,极不“温柔”,孩子们那细皮嫩肉的小手和脸蛋,常常被擦得红红的,生疼生疼的。
洗手洗脸的手巾将就,那洗脸水也莫不如此。平常好说,乡下水不花钱,只是付出点气力。从挑满水的瓮里舀出来洗就是了,但一到天寒地冻的冬天,那麻烦就来了,总不能用带着冰冰凌碴的水洗手洗脸吧。有些人对农村贫穷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缺吃少穿上,岂止如此,那贫穷的简直太到位了,烧柴就是其中一个难题。因少薪缺烧,乡亲们被逼得一到昼短夜长农活少的冬季,宁可忍受着天寒挨冻,也由一日的三餐为省柴改为两顿,难怪俗话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排在第一位呢。自然起床和饭前的洗手洗脸,就成了问题。乡亲们是决不专为洗手洗脸而单独费柴烧水的,那咋办?人们只好借伙烧火做饭时盛上一碗水,连同干粮一块摆放在锅里的篦子上,一起熥热。饭做中了,掀锅吃饭先把水端出来倒入脸盆,一家人便趁热围着脸盆洗手洗脸了,这成了冬天全家人饭前的总动员和统一行动。
天冷物寒,可怜巴巴的一碗热水倒入脸盆,十来只手啊,洗着洗着,水不是凉了,就是变成泥汤子,看着那个寒碜。性情开朗却让母亲常拿眼剜楞斥之为穷不蔫烂、嘴呱哒的父亲,这时总爱自嘲调侃,什么“庄稼汉两把半”啦,什么“是水净的泥”啦,“不干不净才不生病”啦,逗引大家。话是这么说,其实父亲才心知肚明哩。一家人都使一块手巾,同用一盆洗脸水是很不卫生很不讲究的,要不平日里他怎么会说“一病病一窝”、“落门不落人”呢,但知道又会怎样?
多少年来,冬天一家人靠一盆水洗手洗脸的窘况差不多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中叶。直到一个叫“好东西儿”的出现,才结束了这一窘困的局面。
村东头老槐树下的五更爷爷自年轻就有爱喝茶的习惯,好茶喝不起,就专买走街串巷小贩的廉价、粗糙的大叶子生坯茶,实在喝不起了,就喝老伴坡里刈来晒干的茶棵子(罗布麻)、婆婆丁(蒲公英)接济。
爷爷喝茶都是靠奶奶烧火做饭时,把先烧开锅的水舀出来浸壶泡茶,然后再盛上一盆盖上盖垫,放置炕头上用被子捂好保温冲茶。这一来给烧火做饭的奶奶添了不少麻烦,常常遭到奶奶的揶揄,“还喝水喝浆呢,一个眼的驴连踢带咬毛病还不少来”。
一年春节的前两天,在济南参军的大女婿给五更爷寄来了一样东西。一个装订的长方形的木盒,上面标有“小心轻放”的字样,邮递员说,这样的邮件必须要收件人当面验收,说着随手从挎包里掏出一把起子,小心翼翼地将木盒拆开,见邮件完好无损,便欣喜地告诉二老,这是一把暧壶,是盛热水用的,喝水方便着呢。只见一个带把的竹篾子编的外壳,内罩一个银光亮闪闪的圆筒形带口的东西。临年了,因邮件多,邮递员小伙也没顾得多寒喧几句。为赶任务,便急当马活的出了门,蹁上车子,飞也似地走了。
五更爷真是喜出望外,他接过暖壶那个高兴啊,激动地两手还不住的颤抖呢,他感叹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的宝贝东西?这也难怪,那时在我穷乡僻壤的家乡,人们不仅没见过,甚至连听说都没有。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地捧在手里,一个劲地看呀,瞧啊,瞅啊,仿佛一定要看出它热水的机关和名堂来,在一旁的老伴不耐烦了,嗔怪道,你还不把它吃了,一个瞎字都不识的死庄稼腚,还想瞅出个子丑寅卯四五六来?老爷子被呛白的乖乖地把暧壶放到了桌子上,嘴里却不停地嗫嚅道,就一个竹篾笼子罩一个玻璃瓶瓶嘛。看来老爷子可真有些云里雾里了。老伴说,甭瞎琢磨了,今晚做饭我就先把热水灌上,待上一宿,明早看看,不就东发亮下雪,一明二白吗?
这一宿,老爷子躺在炕上反来复去地真没睡好,是高兴激动,还是老挂着暧壶热水的事,他想,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那水在玻璃瓶待了整整一宿,甭说热,就是喝着不炸牙,也算烧着高香哩。第二天起来,急于见功效的他,揭开壶塞,捧起暖壶不以为然地张大口对着壶嘴就喝,这下可不得了了,那水烫得比毒蝎蛰着厉害多了,本该是本能地张嘴把水吐出来的事,却因烫的他慌了神乱了阵脚,不知所措地竞把暖壶也拽了出去,满是燎泡的嘴还喃喃骂道,“他娘的,还真是个好东西儿”。这段故事传出后,不仅成了乡亲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而“好东西儿”也成了我们单寺人暖壶的代名词和歇后语。(单寺暖壶——好东西儿)
此事发生没几个月,济南产的大明湖暧壶就在农村供销社门市大量的面市,因物美价廉、惠及百姓、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暖壶也便成了百姓日常生活的普通用品。自此,也结束了家乡多少年来,一到冬天,一家人只靠借伙烧火做饭熥一碗水洗手洗脸的历史。
我离家在外工作几十年了,以前每次回家,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常年累月挂在屋门上的机裙子,它如同家人见了那么亲切、亲近,旅途的劳顿艰辛,旋即就被到家的感觉所融化。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小康路上,乡亲们普遍住上了“洋楼”,那吊着机裙子的木门早已被整洁透亮的玻璃屏风所代替。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时过境迁,伴我童年成长的机裙子再也不见了,心里还茫然所失空空落落呢。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家乡今后的日子变得多么富足,儿时洗手洗脸的过往是从心里很难抹去的,大概应验了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诗句“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