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宗大历年间,陇西书生邵师老携书童负笈远游,往太原方向求学。时值深秋,草木萧瑟,行至太原郊野,忽见两猎户扛着猎物自山道而下,其中一只赤狐犹在微弱挣扎,眸中似有泪光。邵师老素来心软,见状不忍,遂出钱买下,寻得附近医者为之疗伤。是夜投宿客舍,忽闻房中窸窣作响,起身掌灯,竟见一青衣文士立于榻前,面如冠玉,目若寒星,对着他深深一揖:“恩公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邵师老惊愕不已,那文士却含笑自陈身世:“我乃山中狐族,排行二十,人称二十少。今日若非恩公相救,已成猎人囊中之物。”言罢又拜。邵师老虽知遇异类,然观其举止温文,谈吐清雅,惧意渐消,遂唤店家备酒菜相待。二十少言语诙谐,见识广博,从上古逸闻到当世诗文,皆能娓娓道来。两人把酒言欢,竟生相见恨晚之感,当夜便焚香结义,以兄弟相称。
二十少既无俗务缠身,便随邵师老同往长安游学。抵达长安后,二人赁居新昌里一处清净小院。白日里或访名刹古寺,或游东西二市;夜晚则对坐窗前,一壶浊酒,半轮明月,谈诗论文至深夜方休。
这日黄昏,二人信步至古寺巷。恰逢一顶青幔小轿自朱门内抬出,轿帘被秋风掀起一角,现出轿中女子半张侧脸——眉如远山含黛,目似秋水横波,只惊鸿一瞥,便教邵师老魂飞天外,呆立巷中,直至小轿远去多时仍动弹不得。回到寓所,他茶饭不思,只对烛枯坐,眼前尽是那抹惊鸿影。二十少见状笑道:“贤弟这般模样,莫不是魂被勾走了?”邵师老赧然长叹,将心事和盘托出。
“这有何难?”二十少抚掌道,“若贤弟真心倾慕,愚兄愿为牵线之媒。”邵师老闻言大喜过望,起身便要行礼,被二十少扶住:“且慢,待我先探明那女子来历。”
不过半个时辰,二十少便穿墙而归,衣袂带风:“打听清楚了。此女乃霍王幼女,闺名珠玉,生母原是霍王爱妾。霍王薨后,其母殉葬,这珠玉郡主因系庶出,不为王妃所容,被逐出王府,如今只带两个老妈子、一个小丫鬟,赁居在古寺巷深处小院。”见邵师老急欲追问,二十少摆手笑道:“莫急。这女子心性孤高,须得徐徐图之。今夜我先入她梦中,扮作你的模样与她相会。待时机成熟,你再登门求亲不迟。”
此后数夜,二十少每至更深便悄然离去。邵师老辗转难眠,既盼佳音,又恐唐突。第七日破晓,二十少面带倦容归来,眼中却含笑意:“成了。珠玉已对梦中郎君情根深种,今日便可上门提亲。”
邵师老忙备下厚礼,整肃衣冠,叩响古寺巷深处的木门。应门的老妪听明来意,迟疑片刻方引他入内。庭院虽小,却植有几株丹桂,正值花期,甜香袭人。珠玉隔着竹帘相看——帘外青年长身玉立,眉目清朗,竟与连日梦中之人分毫不差!一时心如鹿撞,羞红了脸,低声对老妪道:“婚姻大事本应由父母做主,可我如今孤苦无依……但凭嬷嬷做主罢。”语虽含蓄,心意已明。
当夜邵师老便留宿小院。红烛高烧,罗帐低垂,他见珠玉云鬓半偏,星眸含羞,比白日更添娇媚,不觉痴了。珠玉轻声道:“那几夜梦中相见,郎君也是这般看我。”邵师老心中暗叹二十少手段玄妙,口中却温言软语,极尽缠绵。两人如胶似漆,在小院中过了两月有余。珠玉恐长久非计,几番催促完婚,邵师老遂雇了两辆马车,带着珠玉、二十少并几名仆从,启程返回陇西故里。
行至陇西,邵师老将珠玉安置在城中别院,留二十少相伴,自己携书童先回家中。邵母见儿子归来,自是欢喜,然听闻他欲娶霍王庶女为妻,顿时沉下脸来:“我儿糊涂!她虽是王女,却是姬妾所生,又被逐出家门,怎配做我邵家正室?”不等邵师老辩解,又正色道:“你表妹姚氏,出身陇西名门,性情贤淑,我早为你定下这门亲事,只待你归来便商议婚期。”
邵师老素来畏惧母亲,见其态度坚决,竟不敢再提珠玉之事。母亲又命家丁严加看管,不让他踏出大门半步。他心中虽念珠玉,却更惧母亲威严,只得终日闷坐书房。
转眼十余日过去,别院中的珠玉望眼欲穿。这日黄昏细雨潇潇,她终于按捺不住,央求二十少前去探问。二十少冒雨而去,夜半时分竟穿墙直入邵师老书房,见他独对孤灯,冷笑道:“好个负心郎!珠玉以千金之躯托付于你,你竟在此安坐?”邵师老面红耳赤,嗫嚅道:“家母之命,实在难违……”二十少厉声道:“你若真心待她,现下便随我去见她!你父母那边,自有我来分说。”说罢一把抓住邵师老手腕。邵师老只觉身子一轻,竟随风而起,不过片刻已落在珠玉闺房之中。
珠玉早已备好酒菜,见情郎忽至,喜极而泣,拉着他手絮絮诉说相思之苦。二十少黯然退出,独坐中庭,听秋雨敲打芭蕉声声碎。
房中,珠玉斟酒布菜,柔情万种,邵师老却如坐针毡。酒过三巡,他忽然推开酒杯,硬起心肠道:“你我缘分已尽,你……另择良配罢。”珠玉手中玉箸落地,怔怔望他良久,泪如断珠:“女子从一而终,郎君教我往何处去?”邵师老垂首不语。那一夜,珠玉的哭声似秋虫哀鸣,时断时续,直至天明。邵师老始终未发一言,天色微亮时踉跄离去。
三日后,二十少面色惨白闯入邵家,对正在习字的邵师老嘶声道:“珠玉悬梁自尽了。她留书说生不能为君妇,死亦当为君魂。”邵师老手中毛笔坠地,墨污了宣纸,却强作镇定:“我与她并无婚约,她的后事……我不便出面。”二十少仰天惨笑,忽然抽出怀中匕首,“嗤”地割断自己一片衣角掷于地上:“今日割袍断义,从此恩断义绝!”言罢拂袖而去,身影没入晨雾之中。
次年春,邵师老奉母命与表妹姚氏成婚。新婚之夜,红烛高烧,姚氏容貌端庄,嫁妆丰厚,确系佳偶。邵师老渐渐将前尘往事埋入心底。谁知半月后,他正与姚氏在房中闲话,忽见纱帐后有一美少年身影,对着姚氏含笑招手。邵师老惊怒交加,一把掀开纱帐,却空无一人。姚氏茫然不解,邵师老疑窦丛生,从此种下心魔。
又过月余,二人游园归来,一枚缀着相思豆的同心结无端落入姚氏怀中。邵师老勃然大怒,认定姚氏与人私通,任她如何哭诉辩解皆充耳不闻。此后家中风波不断,邵师老动辄打骂,最后竟闹至公堂,一纸休书遣返姚氏。
寂寞难耐中,邵师老与婢女暗通款曲,纳为妾室。然猜忌已成痼疾,某夜醉归,疑心小妾与护院有私,狂怒之下失手将其打死。此事虽用钱财遮掩过去,邵师老却再难在陇西立足,只得远走广陵散心。
在广陵,他结识一位柳姓歌伎,色艺双绝,温柔解语。邵师老为其赎身,另筑金屋藏之。初时倒也恩爱,可他疑心病日重,每次外出归来,必翻箱倒柜搜查,甚至拆墙掘地,寻找臆想中的“奸夫”。柳娘不堪其扰,某日趁他外出,携细软远遁他乡。
此后十余年间,邵师老又三娶三弃,皆因无端猜忌不欢而散。晚年时,他性情越发乖戾,婢仆尽散,独居老宅。每逢雨夜,常对灯自语,时而痛哭流涕,时而厉声咒骂。邻里私下传言,这是霍王女珠玉的冤魂作祟,教这负心人永世不得安宁。
却无人知晓,那些倏忽闪现的美少年身影、无端出现的信物、乃至深夜传来的诡异笑声,皆是一只孤愤的狐狸二十余年不曾间断的报复。二十少常隐身形立于邵家屋檐,冷眼看那负心人在自己织就的猜忌罗网中苦苦挣扎。他曾有机会施以更酷烈的报复,却终究选择了这种凌迟般的方式——因为最痛的惩罚,不是肉体的消亡,而是让一个人在无尽的自我怀疑中,慢慢疯魔,最终孤独地腐烂在亲手构筑的囚笼里。
大历末年的一个冬夜,邵师老僵卧病榻,气息奄奄。恍惚间,他见珠玉着大红嫁衣飘然而至,对他嫣然一笑,伸手来牵。他惊恐大呼,却发觉那不过是窗外被风雪卷起的破旧红绸。油尽灯枯之际,他似乎又看到二十少立于床尾,依旧一袭青衣,目光悲悯如初见那夜。邵师老喉头咯咯作响,想说什么,却终究未能出声。寒风穿堂而过,吹灭了最后一盏残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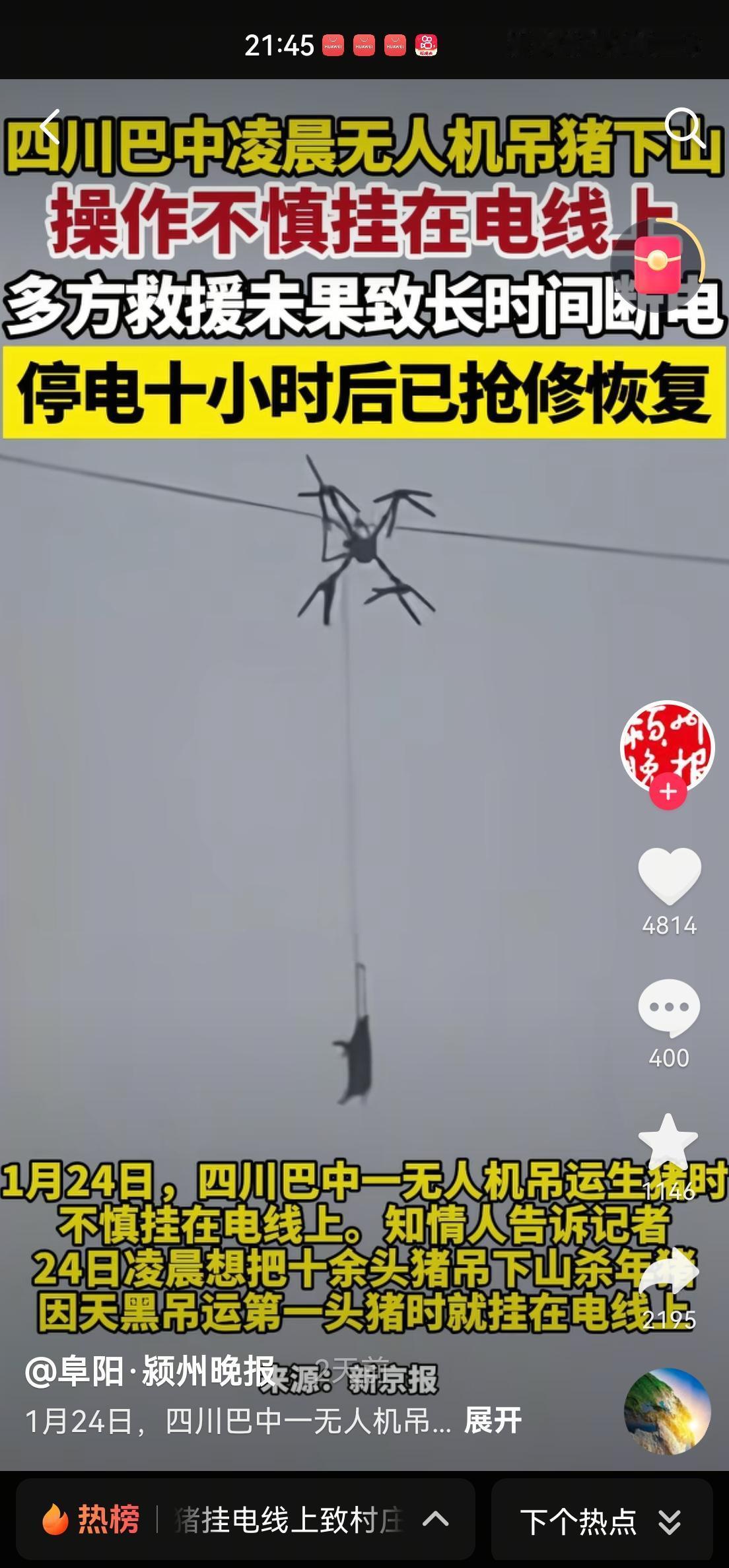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