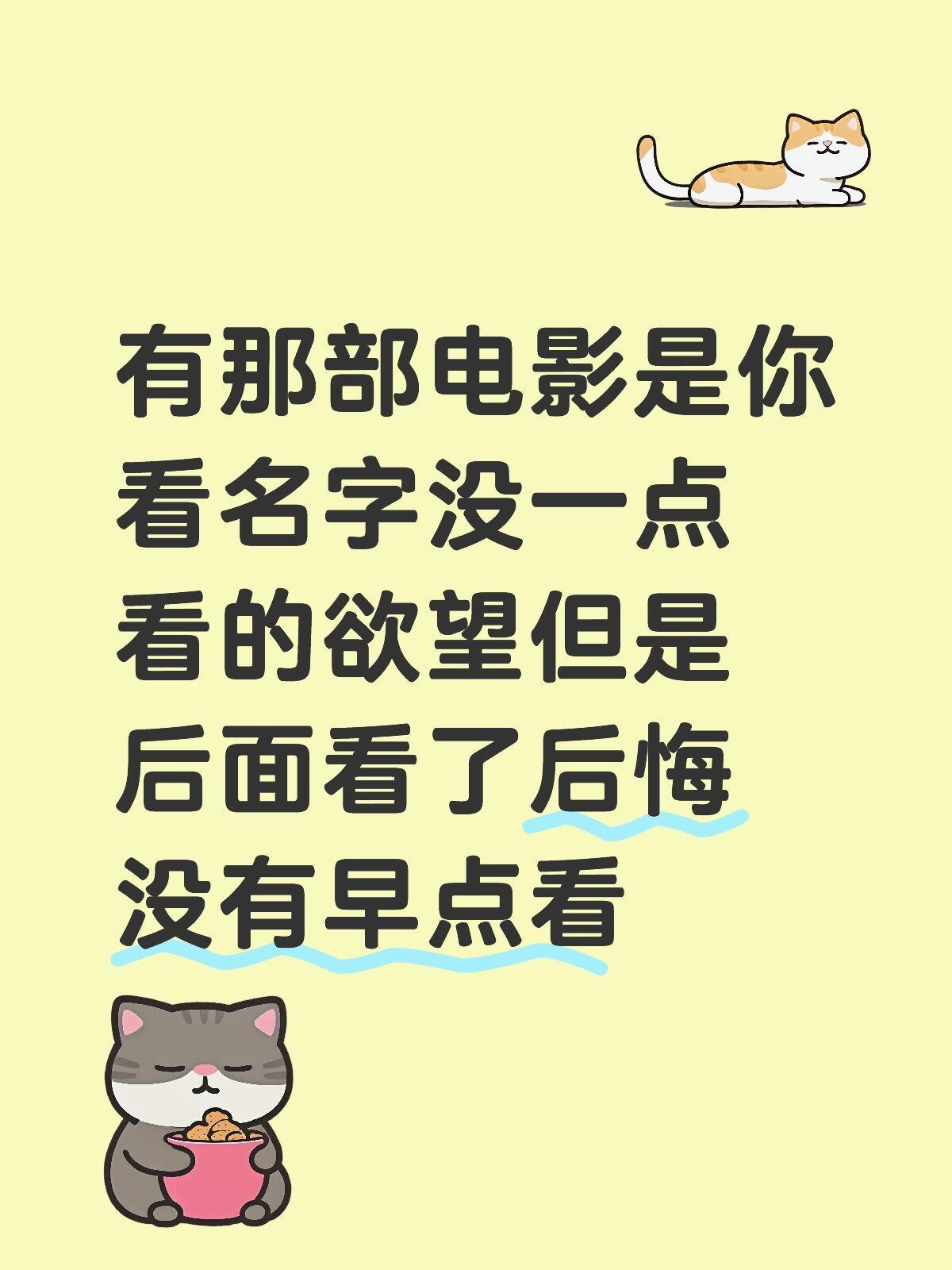六七十年代那时候的中国,几亿人在物资缺少的日子里,精神世界被一种特别的艺术形式填满——样板戏。
那会儿没网络,也没手机,连电视机都稀罕,大伙娱乐的可选不多,在这光景下,样板戏就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文化生活的主要来源。那么官方指定的这些作品,是怎么影响一代人思想的?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样板戏这个概念正式确立。最初的八部作品分别是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交响乐《沙家浜》。
这些著作都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塑造的都是那种“高、大、全”的革命英雄形象,李勇奇、沙奶奶、少剑波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些称呼,比现在任何网红都有影响力。

样板戏的创作按照严谨的“三突出”准则来,就是在所有人物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
演员们要“十年磨一戏”,每个动作、每句台词都经过反复推敲。一个亮相要练上百遍,一句唱腔要磨几个月。
如此追求完美的创作态度,于艺术领域已达较高水准,众多唱段至今还被专业京剧演员视作技艺上的典范。

七十年代初,还有《平原作战》《龙江颂》等9部作品出现,官方不再把它们称作“样板戏”,而是改成叫“样板作品”,这个细微的变化,显示出政治风向有一点转变。
所有样板戏都被拍成电影,这使得它们的影响力大幅提升,从城里的影剧院到乡村的露天场所,样板戏电影成了众人娱乐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郊外的田地里,搭戏台的那个地方特别热闹,太阳刚往西偏了一点,晒谷场上来了好多人,小孩子赶紧搬着小凳子去抢座位,妇女们抱着正在睡梦中的孩子,男人们嘴里叼着旱烟,聚在一起聊天。
放映员支起两根竹竿,把那块有点泛黄的幕布挂上去,这儿就成了全村最像那么回事的地方,当对焦的光线照到幕布上时,调皮的孩子们就会跳起来,用手弄出各种各样的影子,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最让人满心期盼的就是“送片”的那个时候,隔壁村子的电影放映完之后,放映师傅就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后面车架上绑着一个铁箱子,车铃一响,“叮铃”一声特别清脆,一下子整个场地就热闹起来了。
一部《智取威虎山》可以放映好几十遍,村民们在观看的时候可带劲,要是看不到正面的人,就走到幕布后面去,看反面的影像。

有人大胆地爬上草垛、碾盘,还有人爬上那歪脖树;影片放到精彩的时候,常常能听见“扑通”一下,又有人从树上掉下来了。
有个年轻人看《地道战》入了神,竟然从房顶上滚了下来,好在掉在了柴草堆里,没有受伤。第二天全村人都拿这件事开玩笑,可是到了夜里,他又第一个爬上了房顶。

城里的孩子对看电影也十分期待,而且还有一定的仪式感。放学的路上,只要看到操场上拉起了布幕,他们马上就兴奋起来,连书包都顾不上放下,就急忙往家跑。
吃饭期间,也老是心思不在这儿,眼睛一直往窗外瞅,特别希望天快点儿黑,与此同时还害怕突然下雨,只要一瞧见雨滴把放映电影的幕布给淋湿了,放电影的那个人就会开始整理设备,那种失落的感觉,比考试没及格还要难受。

放映样板戏电影的时候,场面更加热闹,公社的干部得出来讲上几句,民兵也得去维持现场的秩序,观众们则要安安静静地、一声不响地观看。
但《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打虎上山那一段,全场还是会响起热烈的喝彩声,唱完以后,田垄里面全是模仿杨子荣摆姿势的孩子,嘴里传出“嘿嘿嘿”的笑声,这是在学习京戏里的笑法;返回的时候,山路弯弯曲曲的,手电筒的光一明一暗,大家还在谈论剧情。

样板戏的唱段就像流行歌曲一样,在我国各个地方都能够听到;工厂车间的广播播放《红灯记》,田野中的扩音器里也传出了《沙家浜》的旋律。
孩童们玩游戏时学着杨子荣打虎上山,大人们干活儿的时候哼着“临行饮娘一碗酒”,就连不认字的老人家,也能有模有样地来上那么几句“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很有趣的是,《沙家浜》里反派胡传魁的唱段——“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成了大家爱模仿的经典片段。

70年代中期,国外的电影慢慢流入中国,这些影片就像一扇扇小小的窗户一样,让一直看样板戏的观众,一下子瞧见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里,船长在甲板上环抱妻子跳舞的场景,让不少青年脸红心跳,朝鲜的《卖花姑娘》让整个影院里的人都哭了,散场的时候,地上全是擦眼泪的纸巾。

阿尔巴尼亚的反间谍片让人摸不着头脑,敌我两边的人长得特别像,看到最后都很难分清谁是好人,
日本电影《追捕》和《望乡》在中国引起很大震动,高仓健演的杜丘冬仁成了很多中国男子模仿的对象,
他们跟着学他的样子,皱着眉头,把衣领竖起来挡风,即使在骑车的时候,也总是用一只手握着车把,模仿他开飞机时的姿态;真由美骑马救杜丘的那一段被反复地观看,姑娘们悄悄地把辫子散开,男生们则在课桌上刻下“杜丘”这两个字。

《望乡》引发的争议,比电影本身更值得人们好好思考,银幕上出现南洋妓院的竹帘画面时,总有一些人愤怒地起身离开座位,把椅子摔得很响。
第二天早场的时候,那些“义愤填膺”的人又出现在后排角落,有中学教师公开指责电影“伤风败俗”,可私下却偷偷问放映员:“有没有未剪辑的版本”。

样板戏跟外国影片在服饰风格上差别还挺明显的,就拿外国影片来说吧,真由美穿的那条连衣裙会被微风轻轻地吹动;再比如在《望乡》这部影片里,和服的腰带是随意系在腰上的。
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一向穿着非常挺括的制服,即使有补丁,也缝得十分整齐,有一次放映《沙家浜》时,阿庆嫂的围裙系歪了,没想到竟然收到了观众寄来的信,说这“把英雄形象给破坏了”。

表演方式的对比更为明显。高仓健一个眼神就能传递千言万语,而样板戏的英雄必须把每种情绪都唱出来。杜丘冬仁被冤枉时的沉默,比郭建光“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二十句唱词更有冲击力。
爱情的表达形式那可是多种多样——真由美讲道:“我是你的伙伴”,这让观众心里特别激动;可在样板戏里的那些革命情侣,他们最亲近的举动也就只是互相递上一把手枪而已。

观众的反应也不一样,看《海港》的时候,领导出场大家会一起鼓掌;看《望乡》的时候就是有人抽噎,散场后很久都很安静。
样板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生活,外国影片展现人们实际怎么生活,当杜丘冬仁在东京街头逃亡时,中国观众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英雄也会害怕,也会犹豫,也会需要女人的帮助。
这种真实的人性光芒,比任何完美的英雄形象都更有生命力。

好比有位观众在日记里这般写道:“看了二十年那始终如一的英雄,总算是见到会流血的人”,此语便道出了样板戏与外国电影最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塑造理想模样的人,后者是刻画现实模样的人。
典范戏这类特殊的艺术形式,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孕育出的产物,也是理解中国文化心理的重要窗口,它不仅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榜样”这一概念的高度重视,也揭示了集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情感所产生的压制作用。
英雄人物很完美,反派角色很丑陋,这种非此即彼的角色设定,让复杂的人性变简单了,也让艺术的真实感降低了。

截至当下,样板戏已然成为过往之事,不过其产生的影响仍持续存在,当年伴着样板戏成长起来的那些观众,现今都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
他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乃至人生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样板戏的影响。这个时候通过外国电影看到的另一种可能性,也成为他们思想解放的重要契机。
文明的力量常常能够超越时代,革命样板戏中所塑造的那些英雄人物虽然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其中所传达出的忠诚、勇敢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依然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外国电影展现的多样人性,给中国观众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角度,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一起构建起一代人的精神基础。
回顾那个特殊时期的电影文化,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还有人性想要突破束缚的力量。
不管是挤在乡村的晒谷场看样板戏的农民,还是在城市的电影院里悄悄看《望乡》的年轻人,大家都通过自己的办法去寻觅精神寄托。

电影乃是二十世纪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之一,在塑造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功用。
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的年代,一块银幕就能连接亿万人的心灵,这种体验在今天已难以复制,从样板戏到外国电影,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次静默革命。

正如巴金所言,令人费解的是,人人平等,样板戏却总是教育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外国电影带来多样视角和国内电影单一叙事碰撞时,中国观众内心慢慢有了变化。

这类变化虽说慢,还不怎么起眼,但却是中国社会迈向开放、多元的关键起始点,你们还记得小时候看样板戏时的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