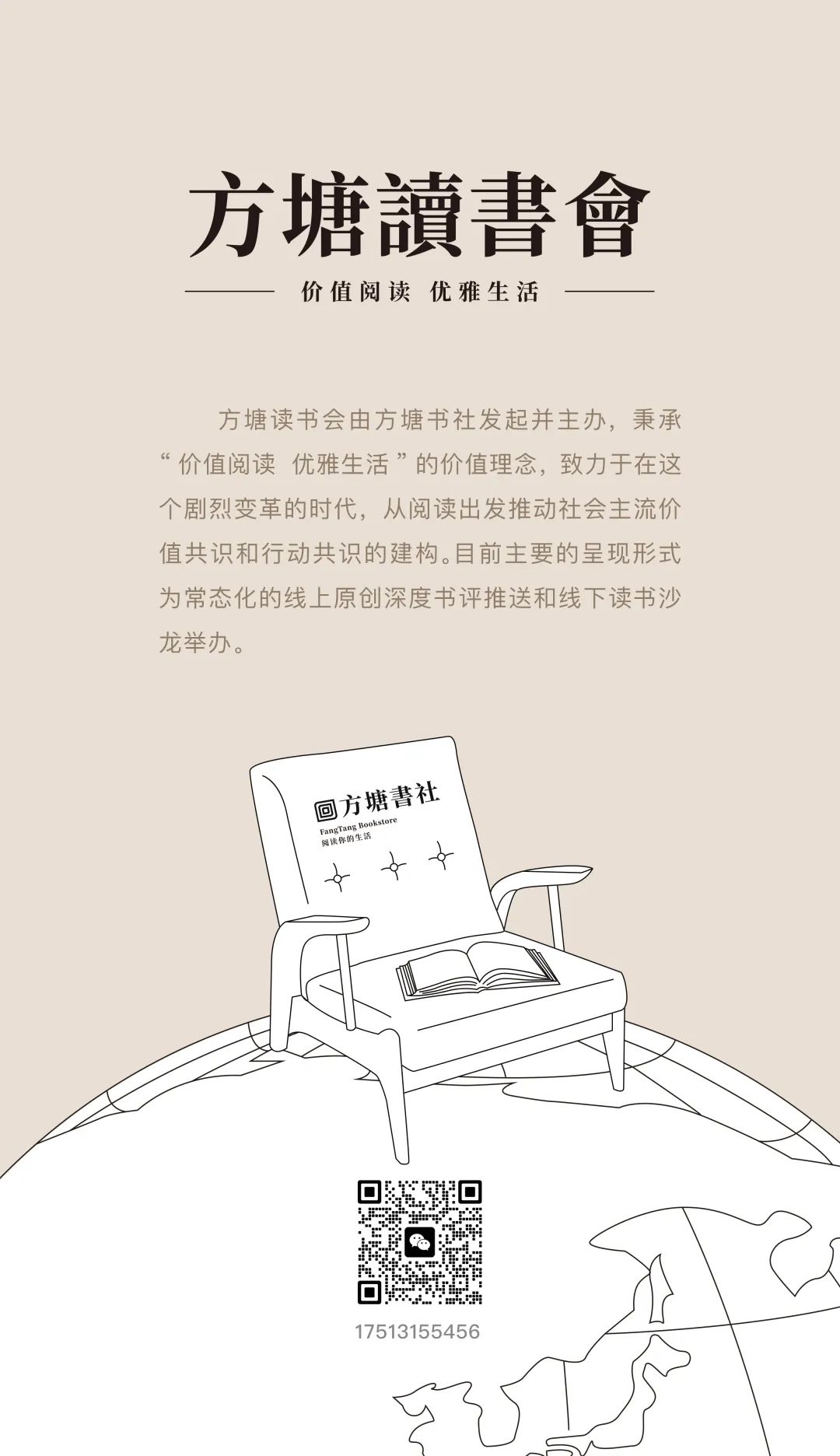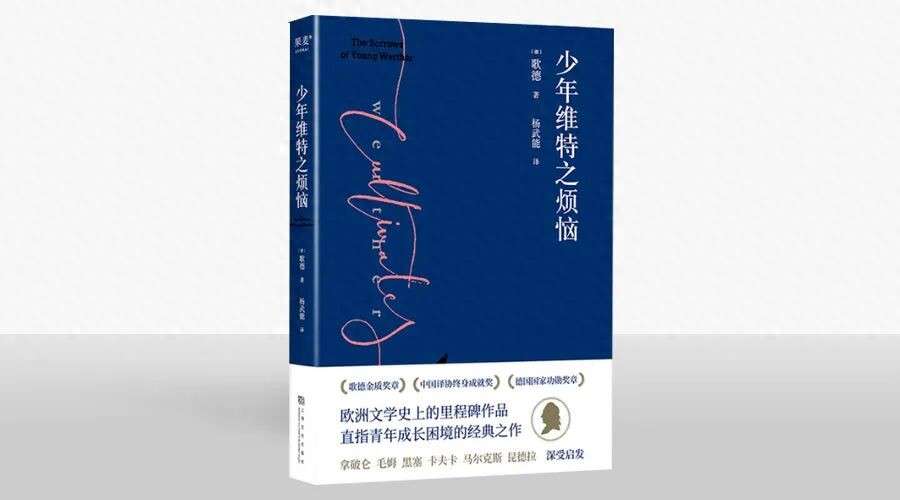
文丨郭翼飞(方塘书社阅读志愿者)
《少年维特之烦恼》叩响了“狂飙突进运动”的门铃,它以书信体的坦诚,呼喊出时代少年人被压抑的心声,成为第一部在欧洲乃至世界引发巨大反响的德国小说。
正如歌德自己所说:“这部小说让人易于理解地、公开地展现了青年内心的病态的痴心妄想,它便到处引起反响。”
在中国也是如此。郭沫若先生的译本让“少年维特”的名字扎根中国青年心中,无论是曾经,还是现在,那些关于爱、理想与孤独的困惑,都跨越时空,并引发强烈共鸣。

【一】
自然是世界的主体,赤诚是生命的底色。少年维特初登场时,是“自然主义的化身使者”——他的信笺里满是生活的暖意。
他眼中的世界是“可触摸的诗”,不是被规训过的“风景”,而是能与灵魂对话的存在。他会在黄昏时坐在河边,看夕阳把河水染成金红色,觉得“河水在替我诉说没说出口的话”。他会在林间散步,听树叶沙沙作响,认为那是“自然在和我谈心”。
他眼中的人类是“剥离礼教后的纯粹”。他不喜欢贵族间的虚伪应酬,却偏爱和村民相处,比如,看绿蒂抱着弟妹喂饭,他觉得“那是人性最温柔的样子”,听老工匠讲自己的手艺,他感叹“认真生活的人都在发光”。他坚信人之初本无隔阂,是客套与规矩把人变得疏远。
他对事件走向的态度是“跟着心走,不问结果”。初见绿蒂时,他明知她已与阿尔贝特订婚,却还是被那份真诚的温柔打动。他不认可理智该压倒情感的世俗逻辑,觉得“喜欢一个人不是错,隐瞒真心才是”。
于是他像飞蛾扑火般靠近,哪怕知道结局可能是灼伤——世界从暖洋洋的亮色变成只有绿蒂的绿色,又在爱而不得的绝望中,慢慢沉向黑暗。就像他在信里写到的,“我像被锁在笼子里的鸟,明知飞不出去,却还是忍不住撞向栏杆。”

【二】
如果此地不属于我,那么我就远走他乡。绿蒂的婚礼成了压垮维特的第一根稻草,在家人朋友的劝告下,他带着“找回自己”的期待离开伤心地,却一头撞进了更冰冷的“交际场”。
初入官场时,他曾试着适应,学着说客套话,按流程处理公文,甚至强迫自己参加那些毫无意义的宴会。可他很快发现,这里的规则比爱而不得更让人窒息——领导表面对他热烈邀请,背后却和同事议论他“太直白,不懂变通”,同事们因为他不迎合潜规则,故意排挤他,把繁琐的杂事都推给他。
他看着那些人用守旧当规律,用虚伪当得体,突然觉得这个社会像“蒙着灰的戏台”——每个人都穿着光鲜的戏服,唱着言不由衷的戏词,没人在乎台下是否有“真心观众”。
于是,理想与现实的割裂,使维特的生活笼罩着感伤主义的色彩。
维特的“感伤”,从来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理想被现实碾碎后的无力。他曾在信里吐槽:“我每天看着他们敷衍工作,却因为‘守规矩’被称赞;我认真做事,却因为‘不合群’被排挤——这世界的公平,难道是按‘虚伪程度’划分的?”
他试图反抗,比如拒绝在不合理的文件上签字,比如直言不讳地指出流程的漏洞,可换来的只有“你太年轻,不懂社会”的嘲讽。
慢慢的,他眼中的世界从空白的迷茫变成压抑的灰色,又在“被排挤的羞愤”中染成愤怒的红色。他终于明白,自己厌恶的不是官场,而是这个用规则扼杀真诚的社会,它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所有“异质”的人都往外推。
此时,感伤成了他对抗世界的唯一方式,他开始躲在房间里读诗,不再参加宴会,甚至不愿和人说话。
可越逃避越孤独,他忍不住问自己:因为世界运转的不公与草率,究竟谁会向他扔出第一块“指责的石子”?是不懂妥协的自己,还是容不下真诚的社会?

【三】
热烈和疯癫,总是在一念之间。维特的悲剧不是突然发生的,从他把手中的书从《荷马史诗》换成莪相的诗歌开始,他内心的“理想”就已经在悄悄转向。
《荷马史诗》里的英雄是“庄严肃穆的理性化身”,代表着他最初对秩序与崇高的向往,而莪相的诗歌,满是“激情澎湃的忧伤”,像极了他后来的处境——那些关于孤独、死亡与思念的句子,成了他内心的“传声筒”。
到了临终前夜,他读的是“悲歌对话”,仿佛提前预知了自己的结局。
福柯曾在《疯癫与文明》中写道:“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文明对‘异质’的排斥——当一个人的思想、情感超出了‘正常’的边界,他就会被贴上‘疯癫’的标签。”
仆人痴恋主人家的小姐,哪怕被打骂、被驱赶也不愿离开,最终被当成“疯子”赶出家门;长工因爱而不得,冲动之下做出极端举动,被社会定义为“狂徒”。他们与维特一样,都是“情感压倒理性”的“异质者”,也都成了文明排斥的对象。
这些“异质”的声音,最终都被归为“疯癫”。维特看着仆人被赶走、长工被指责,突然发现自己和他们一样。
歌德对于维特之死,应该是抱着同情之审判、肯定之否定的态度的,他同情维特的困境,同情他在“爱与礼教”间的挣扎,同情他在理想与社会间的孤独,更同情他真诚被当成错的委屈。
这就像狂飙突进运动中歌德本身就推崇的“青年的激情与自然的天性”,所以他让维特的故事充满共情,读者看到的不是一个“疯子”,而是一个“太执着于真诚”的青年,一个被世界逼到绝境的理想主义者。
维特曾在信里写:“我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除非让我回到自然,回到绿蒂身边。”可歌德通过绿蒂的痛苦、阿尔贝特的叹息告诉读者,“毁灭不是解脱,逃避不是答案”,他认可青年的激情,却也想提醒他们,真诚值得坚守,但不必用生命去对抗世界,就像阳光会穿过乌云,真诚也终会找到容身之处,哪怕需要多一点时间。
不轻易审判他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局限。少年维特之烦恼从来不是维特一个人的烦恼,它是所有青年在“成长为大人”时都会遇到的困境:如何在保持真诚的同时适应世界?如何在坚守理想的同时不被伤害?
如今,这份烦恼,跨越了两个世纪,仍在叩击着每个青年的心灵。所以说,少年维特的故事,早已不是“悲剧”,而是一面镜子,让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看到了自己心中的“维特”,也让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懂得,真诚从不是病态的痴心妄想,而是支撑我们对抗世界的勇气。
编审:汤一凡丨编辑:汤一凡丨设计: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