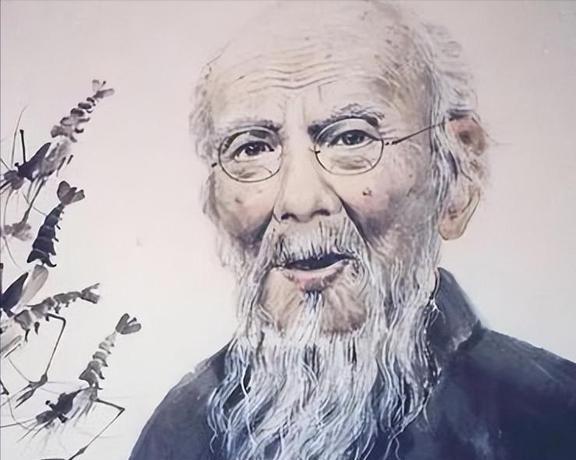《逼嫁》
作者:阮阮阮烟罗

精彩节选: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七年前,蒙难落魄的谢家在长安城是世人避之不及的存在,但现在,却是炙手可热、高攀不起。
昔日艰难支撑门庭的谢家二郎谢殊,如今已是朝中最年轻有为的权臣,他年方二十余岁,就已官居二品尚书,并入内阁,乃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阁臣。
如果阮文源早知谢家还能翻身再起,早知谢二郎来日会在官场扶摇而上,他这区区七品京官,定会携一家老小,牢牢抱紧谢家的高枝,只是现在,说什么都已晚了,谢家的高枝,阮家是决计攀不上了,而谢殊谢尚书,阮家是万万不能再得罪了。
昨日,谢尚书派人来通知阮家,说今天将有喜轿到门,迎阮婉娩过门。阮婉娩是阮文源的侄女,原与谢尚书的弟弟谢琰有婚约,七年前谢家出事时,阮婉娩向谢琰递了退婚书,而谢琰在那之后远赴边关,战死沙场,尸骨无存。
显然谢尚书将弟弟的死,完全怪罪在阮婉娩身上,在时隔七年后翻起旧账,以权压人,威逼阮家将阮婉娩嫁给他弟弟的牌位。
官大一级就能压死人,何况谢尚书权高位重,乃是太皇太后和皇上面前的红人。阮文源只能磕首遵命,和妻子秦氏、儿子女儿一起,从昨天接到命令起,就接连去劝侄女认命。
眼看天色渐向黄昏流逝,喜轿就要到门,阮文源心中越发忐忑不安。从昨天起,侄女就没开口说过半个字,也不知是认命还是没认,要是喜轿来时,侄女死活抵抗不从,阮家怕是要遭大难。
寒彻刺骨的穿廊风中,阮文源忧心忡忡地踱至侄女房外,撩起门帘,见室内烧着红炭的火盆旁,妻子秦氏正倚着坐榻,苦口婆心地劝说侄女,“婶婶知道,你心里惦记着裴晏裴大人,可是裴大人如今人在泽州,决计赶不回来,只能认命了……”
阮文源听妻子提到裴晏,也不由深感惋惜。裴晏是裴阁老的长孙,对侄女颇有情意,如今正在泽州公干。在离京去往泽州前,裴晏曾说等他回京就会来阮家提亲,谁能想到裴晏还没回来,谢尚书就突然发难,强逼侄女履行婚约,嫁给他亡弟的牌位。
裴晏对侄女颇有情意,但他的家族却嫌侄女名声不好、出身不够。如今,谢尚书忽然出手夺婚,在裴家人看来,其实是好事一桩,裴家人根本不会出面阻拦,侄女除了认命,别无他法。
阮家也除了认命,别无他法。阮文源本想通过侄女的婚事,攀上权贵之家,但眼下,一家权贵不肯伸出援手,另一家权贵则来势汹汹,高枝是别想攀了,当前只求能不得罪谢尚书,能一家老小安稳地活下去,便罢了。
阮文源心中叹息时,又听妻子哽咽着道:“你几岁时没了爹娘,叔叔婶婶将你接到家里来养,待你像待亲女儿一样。这些年,我和你叔叔如何疼你,你心里是知道的,要不是万不得已,婶婶不会来劝你这些话,婶婶也舍不得你嫁给牌位守寡,可是……可是谢尚书位高权重,我们小门小户,实在得罪不起……”
妻子越说越是伤心动情,连泪水都淌了下来,可是侄女像既听不见她婶婶的话,也看不见她婶婶的泪水,仍是目光静静地望向窗外。
窗关着,除了眼前一片雪白的窗纸,侄女理应什么也看不见,可她仍是长久地凝视着,仿佛可透过那片空白的雪色,望见些什么。她过于白皙的肌肤,在窗下天光中近乎透明,像是如果炭盆的热气扑上来,她会似剔透的冰雪,融化地悄无声息。
自七年前谢琰战死沙场的消息传来后,侄女便常是这副模样,沉静寡言,淡若冰雪,有时能一个人在窗下安静地坐上一天。但,谢家的喜轿就要上门了,这时可容不得侄女这般,阮文源见妻子晓之以情的劝说似乎无用,就要走上前去,拿出做叔叔的威严来。
然他刚要抬脚时,就听侄女轻声说道:“婶婶不必说了,我愿意嫁。”侄女轻低的声音,似一片雪花落在水里,“我愿意的。”
黄昏时,阮家的新嫁娘被侍女扶出闺房,阮文源与妻子儿女作为新娘亲属,陪走在旁。当走至阮家大门时,阮文源等皆瞠目结舌,门外阶下,来自谢家的喜轿素白如雪,轿帘两侧,甚至挂了两道引魂幡,来迎亲抬轿的谢家仆从们,个个都穿着麻布衣裳,仿佛要抬着新嫁娘去冥婚。
可不就是冥婚,阮文源瞥向盖着盖头的侄女,想侄女性子怯弱,要是亲眼看见这情形,怕是会吓得死活不敢出门。门前寒风肆虐,可别将侄女的新娘盖头吹掀了,叫她看见了,阮文源怕夜长梦多,和妻子一起,草草对侄女说了几句善自珍重的话,就令陪嫁侍女将侄女扶进轿中。
为首的轿夫吹起唢呐,阴云积沉的暮色下,“喜轿”渐渐远去,阮文源如同送走瘟神,终于松了口气时,听妻子在一旁叹道:“婉娘以后在谢家的日子,不会好过……”
“与我们无关”,阮文源眼神转厉,正色叮嘱妻子道,“她嫁出去了,就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往后千万别同她再有往来”,又严肃训话儿女,“听到没有?!”
儿女皆唯唯点头,妻子秦氏也道:“我知道的,不用你多说。”原先噙在她眸中的泪水,早已被风吹干了,秦氏拢了拢衣裳,揽着一双儿女往里走,“瞧着像要下雪了,快都回去吧。”
沉重如铅块的乌云随着夜幕压向人间,风中簌簌的雪珠,打在阮家紧闭的大门上,也打在迤逦前行的喜轿上。尽管天冷,但这桩奇事,还是引得沿途不少人家打开窗扉观看,无人言语,就听那一路喜乐吹打,皆被卷挟在呼啸的风雪中,如孤魂野鬼,哭沙了嗓子。
此时谢尚书府中,却是宾客盈门,凡收到请柬的,无人敢不来赴这场冥婚,甚至一些没收到请柬的中低层官员,也想法子托人弄了一张,携了贺礼,进府来攀谢家的门庭。
喜轿到府后,喜娘与陪嫁侍女将新娘扶至正厅拜堂,众宾客围聚观礼,见新娘和牌位行夫妻对拜之礼,皆不由感觉荒诞,但又无人敢在面上表现出来,因此刻抱着牌位、替牌位行拜堂之礼的,正是谢殊谢大人。
当世有闹洞房的习俗,盖着盖头的新娘被送入洞房后,一些宾客本是要跟过去看个热闹,却在走进洞房时不由感到毛骨悚然,理应颜色喜庆的洞房内,挂满了招魂的白幡,说是洞房,却像是灵堂一般。
婚礼的最后一道仪式,是由新郎执喜秤挑开新娘的盖头,但新郎谢琰早就死在七年前,这事今晚只能由抱着牌位的谢大人替弟代劳。
原本众宾客都只是觉得今晚这场婚礼有些荒诞,但对阮婉娩被逼嫁给牌位这事,并无多少同情。这七年里,阮婉娩退婚害死未婚夫的恶名,早就传遍了京中,一个为图荣华逼死竹马的凉薄女子,如今有此一劫,也算是报应。
但当绣着比翼连枝的盖头滑落地上时,众宾客却皆不由屏住了呼吸,负着恶名的凉薄女子,竟生得十分荏弱无辜,她正在无声地哭泣,一双美眸中细泪滚落,如流珠碎玉碾过雪肤花貌,梨花带雨般令人心魂欲碎。
弱质纤纤,如冰雪晶莹剔透,不染瑕疵。在场之人纵皆知阮婉娩恶名,亦不由心生出几分不忍,仿佛她所做下的错事,也并非十恶不赦、不可原谅,仿佛如她这般的柔弱娇娘,天生合该被人怜惜些。
独谢殊铁石心肠,深觉解恨。满目雪白中,他冷眼看一袭红衣的新娘泪水涟涟,只觉心中终于稍稍畅快了些,他满心刻骨的痛恨,唯有用她悔恨的泪水来洗,但眼下这点泪水,远不足以消他心头之恨,来日方长,她欠谢家的,往后,他要她十倍百倍地还回来。
夜深时,风雪更密了,宾客皆已散去,谢殊不用仆从侍随,独自走过覆雪的后园,来到了谢家祠堂。他推开门走进,将弟弟牌位上沾着的雪花都擦拭干净后,方将牌位归回了原处,他为弟弟点了一盏长明灯,低声说道:“二哥已替你将她娶回来了,你安心吧。”
谢殊在牌位林立的阴影下席地而坐,启封了一坛酒,倒了一杯。这坛酒是弟弟小时候亲手埋在树下的,说这是他将来的喜酒,等他长大成亲时,一家人共饮此坛。但如今,谢家只剩下他与祖母,祖母因世事打击,已神智糊涂了好些年,弟弟的这杯喜酒,如今只有他一人能喝。
平心而论,谢殊并不想喝这杯喜酒,他打小不喜阮婉娩,可弟弟谢琰却喜欢得紧,成天巴望着快些长大成亲。然而弟弟的一片痴心,到头来却遭到了无情的背弃,七年前,谢家卷涉进一桩谋反旧案,案情尚未明了时,弟弟从小爱着的未婚妻,就已派人递来了退婚书。
谢殊至今不能忘记弟弟当时的眼神,十五岁的少年在一瞬间红了双眼,紧攥着退婚书的手,捏得骨节格格作响,似要断裂。少年紧攥着退婚书,跑了一趟阮家,回来后便决定从军,他劝不住弟弟,眼见弟弟提剑策马而去,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杯中的醇酒,像是苦的,混着谢家的血泪。谢殊仰饮了一杯又一杯,无法排解的痛楚因苦酒灼烧更烈。长明灯的灯火,似晃映着女子流泪的面庞,谢殊心中更是恨彻,将酒又倒了一杯,起身转走进祠堂外的风雪中,向着远处灯火昏黄的洞房。
众人皆散去后,雪白的洞房中,便只留下新娘一人,这是不会有新郎的新婚之夜,长久的哭泣,令本就身体柔弱的阮婉娩,渐渐心力难支,她弯身伏倒在喜榻上,涟涟不绝的泪水浸湿了喜被上的碧水鸳鸯。
泪水怎么也流不尽,像是过去压抑了七年的泪水与痛苦,都在今夜宣泄了出来。七年前,谢家卷涉进一桩谋反旧案中,京中人心惶惶,皆认为谢家处境堪危,与谢家有牵连者,或将遭到连坐,她的叔叔婶婶,求她写下退婚书,撇清阮家和谢家的关系,他们用抚养的恩情求她,用阮家满门性命逼她,就像如今,在面对谢殊逼婚时,所做的那样。
七年前,她屈从了,她写下了退婚书,纸上短短二十来字,像耗尽了她全部的力气。退婚书送出半个时辰后,谢琰就来到了她的面前,她望见少年通红的双眼,泪水登时夺眶而出,她喉咙哽咽得说不出半个字,就听少年嗓音沙哑地道:“婉娩,你莫哭莫怕,我不是来怪你的,我只是来告诉你,我要走了。”
少年谢琰说,他决定赴边从军,如今边关饱受异族滋扰,他决心奋战沙场,向皇帝证明谢家的忠诚,也建立一番男儿事业,为了谢家,为了她。谢琰道:“婉娩,你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风风光光地娶你为妻。”
少年许下诺言后,便策马决绝离去,她没有来得及告诉他,在送出退婚书时,她心中想的是,她已替阮家撇清了与谢家的关系,如果谢家真要遭灭顶之灾,她会以个人的身份,与谢琰生死相随,如果谢琰被流放,她会跟着他去,如果谢琰被处死,她会在黄泉路上陪他。
她没能说出那些话,往后的日子里,每日都在佛前祈祷谢琰平安归来。然而她最终等到的,却是谢琰战死沙场的消息,谢琰确实在战场上立下了功劳,但是以性命为代价,他在异族夜袭时自请断后,保护了军民成功撤退,自己却惨死敌手、尸骨无存。
消息传来的那日,她在房中坐至夜深,将白绫悬在了梁上。她想要和谢琰一起走,却被乳母发现救了下来,乳母求她别做傻事,说她母亲当年生她时,因难产痛了一天一夜,问她是否就要这般报答母亲的生育之恩。她无言以对,只能断了死志,依然活着,浑浑噩噩地活着。
那之后的七年时间里,她都像是一具行尸走肉,心早已死了,只是仍留有几丝呼吸。谢殊派人上门逼嫁时,世人都以为她愤恨不甘,只是不得不从,可其实,她心里是欢喜的,这七年里,心中浮起的唯一一丝欢喜,为能够嫁给谢琰,成为谢琰的妻子。
在此新婚之夜,压抑了七年的痛苦与悔恨,全都爆发了出来,化作流不尽的泪水,浸湿了绣织鸳鸯的金丝银线。阮婉娩泣不成声时,忽听见洞房房门被人推开,呼啸的风雪随着来人步伐卷扑入室,阮婉娩抬眸望去,透过朦胧泪光,见是谢殊去而复返。
她尚未有所反应时,谢殊已挟着沾衣的风雪,大步走到了她的面前,一把将她拽了起来,要迫她饮下一杯喜酒。冰冷的白瓷抵在唇上,醇烈的酒液呛入喉中,阮婉娩无法承受,被呛得泪意更浓,挣扎着吐出两个字,“……二哥……”
谢殊却打小就厌烦阮婉娩这样唤他,从前,回回阮婉娩来谢家做客,跟随弟弟谢琰唤他为“二哥”时,他心中都会浮起一股烦躁之意,为明明不喜阮婉娩,却还得将她当做未来弟媳对待。
但事到如今,她有何资格再唤他“二哥”,谢殊冷笑着掐住阮婉娩的下颌,硬将融着冰雪的酒液灌入她口中,冰冷俯瞰的目光,似要撕开女子雪玉般的皮囊伪装,扯出内里凉薄无情的蛇蝎心肠。
“‘二哥’?你以为你与谢家之间,还有旧情在吗?!”谢殊嗓音嘲冷,俯身逼近女子滢满泪珠的双眸,“你欠谢家的,到死都还不尽,别想着另嫁他人另谋富贵,只要我活一日,你就一日离不了谢家,我要你这一世都活在悔恨之中,在谢家为阿琰守寡到死!”
他失去弟弟的痛苦一日不消,她就一日不得解脱,谢殊逼迫阮婉娩饮下了她和阿琰的喜酒,酒液尽时,素瓷酒杯在他手中攥裂成片,谢殊将楚楚可怜的女子甩回榻上,冷漠无情地转身离去。
因酒呛喉咙,阮婉娩在谢殊走后,伏榻低咳许久都未平息,眼睫垂缀的泪珠,随咳声一滴滴洇落在榻被上,她默默回想着谢殊几乎狰狞的怒容,心想谢殊是恨透了她,想将她囚在谢家如囚在牢笼之中,可其实,她早就身在牢笼中了,自从谢琰死后,她永是悔恨的囚徒。
谢尚书忽然去而复返时,陪嫁侍女晓霜吓得跪在洞房门外,头也不敢抬,等谢尚书终于离开,走得身影远不可见后,她才敢起身探头瞧看室内情形,将房门关了抵御风雪,又走到榻边,收拾瓷杯碎片,以防小姐不慎踩伤了脚。
将这些都做完后,晓霜也不知该做什么了,被逼嫁给牌位这种事,无论外人如何宽慰,当事人心里都很难释怀,何况小姐本来有一桩将要到手的绝好婚事,就这么成了泡影,小姐这样年轻貌美,往后余生却只能守寡终老,实在可怜。
晓霜怜悯地望着小姐,也沉默地陪伴着小姐。她不敢离开,担心小姐会在夜里无人时想不开,就像七年前那样。七年前小姐想不开悬梁的事,只有她和她娘亲知道,如今娘亲已不在人世,晓霜尽管只是侍女,私心里却与小姐有种相依为命的感觉,不希望小姐出事。
小姐在伏榻许久后,抬起头来,虽面上满是泪痕,眼中却是干涸的,像是已将双眸哭空了。小姐沙哑着嗓子对她道:“你去休息吧,不必守着我,也不必担心我,我不会想不开寻短见的,我还有事要做,代替我的夫君去做。”
晓霜听不懂小姐后半句话,将信将疑地不敢离开,是夜还是守在小姐身边。但长夜漫漫,她终是倦到睁不开眼,也不知何时睡了过去,再醒来后,自己先吓了一跳,忙起身寻找小姐,生怕有道悬梁的纤弱身影,猛地撞入她眼帘中。
却见小姐正在镜台前梳发,小姐已换下了昨夜的大红婚服,穿着一袭雪白的素衣。晓霜走上前为小姐拿取簪钗,又看外面天还未亮,问道:“小姐怎起的这样早?不多休息一会儿。”
小姐声音低哑地道:“我想早些去老夫人那里。”
小姐……是想去服侍照顾谢老夫人……晓霜忽然明白了小姐昨夜的话,小姐不会寻短见,是因想活着替谢琰尽孝,孝顺服侍谢琰的祖母谢老夫人。
伺候小姐梳洗毕后,晓霜打开房门,正要扶小姐出去,就见谢府的管事姑姑走到了门前。那管事姑姑面无表情,虽唤小姐一声“夫人”,却也不对小姐行礼,就僵直着身体,硬梆梆地道:“奴婢来传大人命令,大人令夫人每日服侍老夫人,为三公子抄经念佛。”
谢大人这般命令,应是想惩罚小姐吧,可是,服侍老夫人、为三公子抄经念佛,是小姐本就想做的事啊。晓霜边心想着,边默默看向小姐,见小姐容色平静,声亦轻静地说道:“知道了。”
今日为正月初九,国朝逢三六九例朝,天未亮时,谢殊就已乘轿出门。文武百官在宫门外整队等待时,谢殊作为阁臣,轿子径入位于皇城午门旁的内阁,待外面百官点名入内完毕,已在皇极殿外序班站好,谢殊方与其他几名阁臣,缓缓踱出内阁,率百官恭迎圣驾。
圣主还未满十岁,诸事依赖内阁,早朝时只是聆听官员奏本,不会当场下达任何决断,需在朝后就事问询内阁。辰时散朝后,小皇帝令阁臣随驾至乾清宫东暖阁,在商议政事前,与他一同用些早膳。
阁臣们拱手谢恩后,坐于御座下首两侧,御膳房的小太监们捧来了一桌桌的茶点。阁臣们的早点,除因君臣尊卑,比圣上早膳少了几样外,其余并无不同,小皇帝心地仁善,礼待重臣,颇有未来明主之相。
只是到底年幼,还是孩子心性重,会对新鲜事感兴趣。小皇帝用了几口驼酪粥,乌溜溜的眼睛转了转,脆生生地问道:“朕听说,谢家昨日娶了新妇?”
首辅裴景德与次辅谢殊嫌隙甚深,见此刻皇帝主动问起,就赶在谢殊开口前,回禀皇帝道:“回陛下,确有此事,只是不是谢尚书娶妻,而是他为亡弟娶妻。”又像是在与谢殊随口说笑道:“虽然昨日京中为此热闹了一场,却也有些闲话传了出来,说那阮姓女子其实早与谢家退婚,谢尚书似有逼婚的嫌疑。”
谢殊拨了拨粥碗中的羹匙,微笑着道:“元辅也被流言误了,所谓退婚一说,不过是外人乱传的闲话,谢家从未收到过阮家的退婚书。”
裴景德见谢殊在圣上面前面不改色地扯谎,于心中冷笑了一声。谢殊因曾有救驾之功,在太皇太后和圣上面前十分得脸,裴景德虽是元老首辅,却也时常难抑谢殊锋芒,时日久了,本就心中龃龉越积越深,又因谢殊从去年起,蛊惑天子,借推行所谓新政,打压朝中勋贵老臣,他更是迫切想将谢殊赶出内阁,只是暂时无计可施,只能平日里占几句口头机锋。
裴景德这会儿并非想替那阮氏女出头,只是想借此事在天子面前给谢殊上上眼药,就仍是话中带刺道:“都说死者已矣,生者为大,纵使没有退婚一说,那阮氏女正是青春年华,谢尚书为何不主动解了婚约,放其去自由婚嫁?谢尚书昨日行事,未免……有些刻薄啊。”
谢殊却未回击他的讥讽,面上也无丝毫恼怒之色,仍是笑如春风道:“元辅这样说,是否是为了长孙?下官昨日办完婚事后,才听人说,元辅的长孙裴晏,似对阮氏有意?”
御座上,默默听两位重臣语打机锋的小皇帝,眼睛悄悄地亮了,他在宫中也有听到流言,说是那个叫阮婉娩的女子,本来是要嫁给裴阁老的长孙裴晏,也不知是真是假。
小皇帝好奇心炽烈,边咬着早点,边盯着谢殊,见谢殊十分客气地对裴阁老道:“如元辅是为了长孙裴晏,下官今日回府就替亡弟写下和离书,并以谢家的名义,替阮氏出一份嫁妆,将她人和嫁妆一同送到裴家安置,等待裴晏回京完婚。”裴景德听得眼角暗暗抽搐,他的儿子都是庸碌之辈,长孙却是可造之材,深得他心,他想为长孙来日仕途铺平青云之路,想牵线为长孙迎娶公侯之女,哪里看得上这个阮氏女。本来一个娘家无势的女子,就不配为裴晏之妻,要是裴晏还娶了被谢家扫地出门的女子,那他堂堂首辅的老脸,不就被谢殊按在地上踩了吗?!
裴景德忍着心中恼火,抖了抖唇角,皮笑肉不笑地道:“谢尚书说笑了,你所听到的,也只是无稽流言,不可当真。”
谢殊微微一笑,不再咄咄逼人,只是微垂下长睫,遮隐眸底浮起的阴霾。明明已言语弹压了裴景德,他心中却无畅快之意,为裴景德藏着暗箭的那些话,令他这会儿又想起了阮婉娩与裴晏的奸|情。
数日前,裴晏因公干离京,他也有事去了京郊,轻车简行时,正巧目睹了阮婉娩为裴晏送行的一幕。当时落雪纷飞,阮婉娩擎着的伞倾向裴晏一边,使她羸弱的肩上落积细雪,裴晏映着飞雪的目光定在阮婉娩面上,深情款款地说:“等我回来,我就去你家提亲。”
他放下了马车窗帘,遮绝了视线,而心中腾起了怒恨的火焰。从七年前弟弟不幸离世后,那幽恨的火焰就埋在他心底,他以为七年的时间可以将过去的痛恨渐渐磨平,可其实没有,那火焰从未熄灭。
凭什么他的弟弟死在漠北的冰天雪地里尸骨无存,而阮婉娩却可与别的男子在京郊的风雪中情意绵绵?!凭什么他的弟弟在阴曹地府孤苦伶仃,阮婉娩却可与别的男子卿卿我我、结为夫妇?!
一声声的凭什么,呛着旧日的血泪,时光磨不去恨意,那一天的那一眼,将他深埋心底的怒恨勾连得烈火焚天,他绝不能容忍阮婉娩称心如意,他终是决定逼婚。
如今,阮婉娩已是弟弟的妻子了,他既报复了阮婉娩,也帮弟弟完成了生前的心愿,可为何,心中却还没有多少畅快之意。昨夜逼迫阮婉娩饮下那杯喜酒时,她的眼泪坠在了他的手指上,已经过去一夜了,那泪水的温度,仿佛还萦在他的指尖。
是日谢殊回府时,天已擦黑,他的官轿刚在轿厅落下,迎候在此的管家周敬,就赶上前打起轿帘。谢殊边从轿中走出,边问周管家道:“她今日如何?”
周管家自然知道大人问的是谁,忙回道:“阮夫人今日十分安分……”他刚起了个话头,就听见大人冷笑了一声:“她算哪门子的夫人。”
周管家只能磕磕巴巴地改了口,“……阮……阮氏……”他顺了顺僵硬的舌头,将要禀的话,一气说了出来,“阮氏晨起听到大人命令后,就去了老夫人的清晖院,一日都待在老夫人的院子里,老夫人醒着时,阮氏就照顾老夫人,老夫人歇下时,阮氏就为三公子抄经念往生咒。”
见风使舵是她的好本领,当年谢家出事,她生怕受到半点连累,等不及就第一个跳船,现如今被困在谢家,又立刻懂得何为寄人篱下,装得温淑贤良、安分守己。谢殊听着周管家的汇报,心中冷笑连连,在夜色中走向祖母的清晖院。
清晖院中,阮婉娩正扶谢老夫人到花厅用膳。今日一天,她都在清晖院中陪伴照顾谢老夫人,小的时候,她常被接到谢家做客,常能见到慈爱的谢老夫人,后来谢琰出事,退婚的她,不能也无面目再踏入谢府,在今日之前,已有七年时间,未能这般亲近谢老夫人。
幼年来谢家时,她常和谢琰一起待在清晖院中,玩耍和陪伴老夫人。谢老夫人若只看见谢琰,就会问婉娩哪里去了,若只看见她,就会问阿琰哪里去了,定要他们两个一块儿承欢膝下才好。
此刻,谢老夫人也在张看着问道:“婉娩,怎么不见三郎呢?三郎哪里去了?怎不回来吃晚饭?”
七年前谢家出事时,谢老夫人因接连的世事打击,患上了失魂症,从此神智糊涂不清。似是不幸,却也似是幸事,因患病之后,谢老夫人对于时间的记忆是颠倒无序的,她再不记得谢琰战死沙场的事,在她心里,谢琰无事,好好地活着。
阮婉娩想对谢老夫人说一句善意的谎言,但她不擅说谎,还在心中斟酌词句时,已有男子的嗓音从外传了进来,伴着沉稳的步声,“阿琰在外公干,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是谢殊,阮婉娩搀扶老夫人的手,不禁攥紧了些,眉眼也略略低下。从前常来谢家做客时,谢殊在她眼中是性情沉稳、不苟言笑、有时有点严厉的兄长形象,后来谢琰离世、谢殊平步青云,那七年里,她未再见过谢殊,但听世人议论,逐渐权高位重的谢殊,是如何城府深沉,行事老辣,手腕狠硬。
原本世人议论再多,也只是个虚幻的影子,隔了七年未见的虚影。但当昨夜,那杯醇烈的喜酒被硬灌入她喉中时,谢殊扼制她的力道,强硬得像是能将她按在身下碾碎撕裂,虚影在她眼前屹立如山,在凛冽的风雪中淬成了刚硬冷锐的锋刃,她清楚地认识到谢殊如今是怎样的人物,丝毫不怀疑谢殊在怒极恨极时,极有可能毫不留情地杀死她。
厅内侍仆皆向归府的大人弯身行礼,阮婉娩低着眉眼,听谢殊缓缓走到了谢老夫人身边,谢老夫人嗓音困惑地问谢殊道:“三郎怎么刚成亲,就要外出公干?是去哪儿?要多久才能回来呢?”
谢殊道:“去黎州一带,二十来天就回来了。”
不消担心二十来天后,祖母问阿琰为何未归,因祖母根本就记不清时日。谢殊扶祖母在膳桌前落座,自己陪坐一旁,径将阮婉娩当成侍立布菜的奴仆,但祖母却招呼阮婉娩一同坐下,不解地问道:“婉娩,你怎么不坐?”
阮婉娩瞥了眼谢殊淡漠的眉宇,轻声说道:“孙媳伺候您用膳,这是孙媳应该做的。”
谢老夫人却握住阮婉娩的手,硬让她在她身边坐下,“用不着,我虽年纪大了,但还没到要孙媳喂饭的地步。”谢老夫人笑说着,朝膳桌上菜式看去,见一道干贝银丝羹正摆在谢殊前方,就道:“二郎,你舀一碗银丝羹给你弟妹,我记得她爱吃这个。”
谢殊微微侧目,见阮婉娩垂首默默,不知是不懂得主动婉拒,还是就想在祖母面前拿捏他一回,以报复他的逼婚之举。尽管心中厌恶阮婉娩这般作态,但在祖母的连声催促中,一向孝敬的谢殊,还是不得不起身舀了一小碗干贝银丝羹,递给阮婉娩。
阮婉娩忙起身伸手去接,她本来以为谢殊绝不会为她舀羹,尽管有谢老夫人吩咐,谢殊也会设法推脱掉,没想到谢殊真舀了一碗送到她面前。阮婉娩双手捧接过盛羹的小碗,低头轻轻地说道:“多谢……大人……”
昨夜阮婉娩曾似旧日称呼谢殊为“二哥”,但遭到了谢殊的嘲讽,遂她此刻改口敬称谢殊为“大人”。然而这称呼惹得谢老夫人笑了起来,“怎么嫁过来后,还比小时候要见外呢?!”
谢老夫人笑着轻拍阮婉娩的手,慈爱地道:“这家里没什么‘大人’,只有你的家人。”又特地嘱咐谢殊,“你弟弟不在家,你这个‘二哥’要照顾好弟妹,衣食等都要安排好,决不能委屈了她。”
谢老夫人待她越是慈爱,阮婉娩心中就越是难受,如果她当年没有写下退婚书,也许谢琰就不会死在战场上,谢老夫人也不会伤心到患上失魂症。满心愧疚如千针万箭在暗中对她施加凌迟的酷刑,阮婉娩食不知味地陪谢老夫人用完晚膳,和谢殊一起扶送老夫人回房休息。
待谢老夫人寝房房门关上,她身边的谢殊像立即变了一个人,尽管神色未变,周身却似迅速覆上一重凛冽的气场,稍靠近些就会被寒气冻伤。阮婉娩心中不安,却不能退避,因谢殊语气沉冷地命令她道:“随我到书房。”
谢府有多处书房,谢殊口中所指,乃是竹里馆书室。谢殊如今虽是谢家之主,却未搬至历代家主所住的正房院落,仍是住在他自己从小长大的竹里馆中,竹里馆左右与松风斋、绛雪院毗邻,这三处是谢家三位公子的居所,只是如今,三公子只存其一了。
阮婉娩对竹里馆并不陌生,从前她常被谢琰邀到他的绛雪院吃茶玩耍,在走经过竹里馆时,有时也会被谢琰拉到他二哥院中坐上一坐。记得有次,她还随谢琰到了竹里馆的书房,谢琰说趁谢殊不在,给她看看好东西。谢琰口中的好东西,是一方白玉卧鹿镇纸,谢琰说这是祖传之物,被他父亲送给了二哥使用。
谢琰说着时,语气不免衔酸,为父亲对二哥的偏心。那时他们都年幼不懂事,不知那方白玉卧鹿镇纸,寄予了谢父对谢殊的殷切厚望,谢琰的大哥年幼早逝,谢殊虽行二,却如同长子,要在来日担起谢家的门楣。
那时她和谢琰都年幼,不太懂得那些,谢琰从谢殊书案上拿了那方白玉卧鹿镇纸给她赏玩,她双手捧起,要对着阳光细看时,忽看见谢殊就悄没声地站在门外,惊得手微一抖,将白玉镇纸摔在地上,摔断了一只鹿角。
她吓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谢琰微一愣后,也看见了门外的谢殊,连忙说都是他的错,而她不要谢琰给她当替罪羊,在回过神后,也忙说都是她的错。她和谢琰争相揽错时,只听谢殊冷喝一声“闭嘴”,谢殊走进书房,将白玉镇纸和那只鹿角都捡了起来,而脸上没什么表情。
好像摔坏镇纸这事,没什么大不了,是她和谢琰反应过度了,谢殊脸上没有对此事的苛责,而只是觉得他们吵闹。谢殊将镇纸放回原处,铺开纸笔,说他要做功课了,让谢琰送她回阮家,说罢,就执笔舔墨,练起了专攻科举的馆阁体书法。
她和谢琰愣愣在旁看了一会儿,感觉好像真的没什么事,就听谢殊的话,安安静静地离开了。后来才知,她和谢琰前脚刚出谢家,后脚谢殊就去向谢父告罪,说是他不慎摔坏了白玉镇纸,那镇纸不仅仅是谢家祖传之物,还是大梁朝开国皇帝赐给谢家的。
她和谢琰在阮家的后园喂小鱼时,谢殊被谢父罚到谢家祠堂跪了半天。后来她知道了这件事,再去谢家见到谢殊时,就不由红了眼睛,她觉得很对不起谢殊,她想要和谢殊一起,去跟谢伯父谢伯母说出实情,但谢殊却对她露出了近乎忍无可忍的神色,冷冷说道:“别烦我。”
其实她能感觉到谢殊似乎不喜欢她,尽管她那时候还小,但回回到谢家时,谢家上下同她说话都是衔着笑意的,只有谢殊,总是神色淡漠。此前,她只是怀疑谢殊不待见她,但当那天,真真切切听到那一句“别烦我”后,她终于确认了谢殊对她的不喜,确认谢殊素日淡漠的神色背后,是对她的忍耐和厌烦。
那时她在谢殊心中,就是个会带来麻烦的惹祸精吧,谢殊那时独自揽下白玉镇纸的事,是为了弟弟谢琰,谢殊知道谢琰定会替她担责,所以替弟弟揽错。而后来,她惹下了更大的祸事,犯下了无可挽回的过错,谢殊没有了可以继续保护的弟弟,只能将滔天怒恨,都发泄在她这罪魁祸首身上。
被逼嫁牌位一事,是她咎由自取,可她,也心甘情愿。阴沉的夜幕下,阮婉娩随谢殊走过积雪的竹径,来到了竹里馆书房中,书房灯光亮起时,她见房内陈设与她幼时所见大有不同,唯独那只断角的白鹿镇纸,任凭时光淌逝,仍静静地卧在谢殊的书案上。
侍从点灯后退了出去,书房内,只她与谢殊二人。阮婉娩沉默地站在书案前,见谢殊拿起了书案上的淡黄色写经纸,那是她今日为谢琰抄写的往生咒,本来她早让晓霜送回了绛雪院,但这会儿她所抄写的经文,却出现在了谢殊的书案上。
谢殊在朝廷都有“手眼通天”一说,何况在谢家,且今早是他派人命她抄写经文,这会子算是在检查了。阮婉娩默默时,听谢殊语气讥冷道:“就抄了这么一点?”
今日谢老夫人除午憩时,一直在拉着她说话,她自然不能在谢老夫人面前为谢琰抄经,只能趁着老夫人午憩的那点时间。阮婉娩本无意在谢殊面前为自己分辩,但听谢殊话中对她的讥讽之意,愈来愈重,“要装,也装得像样些,还是你连装模作样的耐性都有限,一心盼等着裴晏回京,救你脱离苦海?”
阮婉娩并没有在心中盼等裴晏归来,忍不住为自己分辩了一句,“我没有这样想。”
谢殊心中冷笑,眼前又掠过风雪中阮婉娩为裴晏擎伞的画面,他半点不信阮婉娩的分辩,嘲讽地道:“你以为裴晏回京之后,会带你离开谢家吗?你不要忘了,你已经嫁给阿琰为妻,私通人妻可不是什么好名声,裴晏这种沽名钓誉之徒,在你婚后,岂会再来沾染你半分?!”
阮婉娩对裴晏并无情愫,但裴晏对她有恩,她听谢殊鄙薄裴晏为人,为裴晏说道:“裴大人品性正直,不是沽名钓誉之人,裴大人他……”
她话还未说完,就听见“砰”的一声,是谢殊将经纸拍在了案上,谢殊像是认定她一心盼等裴晏救她,眸中墨色涌聚,眉宇凝寒,“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安分守己些,你若敢给阿琰戴绿帽子,让他在死后还要遭人笑话,我定叫你生不如死!”
其实昨夜谢殊逼她喝酒时,力气再稍大些,就能当场扼死她了。阮婉娩信谢殊说的出做得到,她低眸避开谢殊漆沉的目光,沉默着咽下未说的话,没有必要再说下去,无论她说什么,恨她入骨的谢殊,都是一个字不信。
室内一时静寂,只听得窗外寒风啸个不停。耳边风声呜咽几回后,阮婉娩眼前灯光一晃,是谢殊抬手将那张经纸收了起来,“以后每日,至少写满十张”,谢殊对她下达了这道命令后,又厉声道,“祖母面前,你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谢殊言下之意,是不许她向谢老夫人诉苦,但谢殊实是多虑了,是她害了谢琰,也间接害得老夫人神志不清,她哪里会有脸面向谢老夫人诉苦半句,阮婉娩在谢殊冷峻的目光下沉默顺从,缺了一角的白鹿,亦在这初春幽夜里,缄默地卧在案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