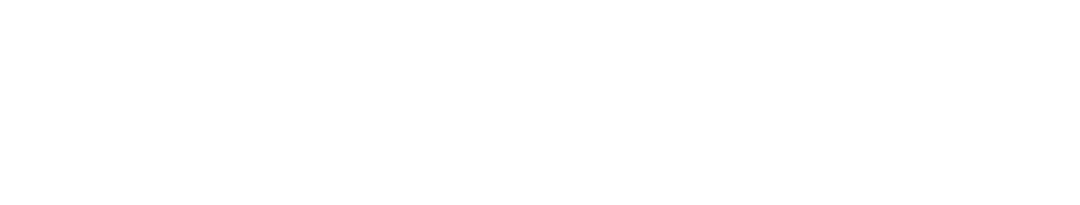

采访、撰文|芝士咸鱼
编辑|野格
十点人物志原创
2022年4月,我们发布《抑郁症,正在吞噬我们的下一代》,首次将目光聚焦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此后几年,又相继推出《休学潮席卷小学生:每天只睡5小时,熬不动了》以及追踪休学青少年去向的《“休学潮”后续:中国超千万抑郁青少年的出路,不止一种》,均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今年是“十点人物志”连续第四年深入探讨青少年心理议题。然而,问题非但未见缓解,反而一年比一年更为严峻。随着大量案例的积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逐渐浮现:许多摇摇欲坠的孩子背后,往往站着濒临崩溃的父母。
父母的心理困境常常被忽视,但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同样真实而沉重。《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显示,20.2%的患儿家长有高抑郁风险,是全国普通人群的四倍;近半数家长(49.2%)感到重度照顾负担,不仅自身心理健康受损,也影响了家庭的整体氛围。

图源:渡过《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
梁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非虚构文学作品“梁庄三部曲”系列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母亲。最初,她只是察觉到自己孩子的情绪变化;随着与更多休学家庭、心理咨询师以及学校校长的深入对话,她意识到,这并非个别家庭的困境,而是一种正在蔓延的时代症候。
于是,她写下《要有光》,从滨海、京城到丹县(除京城提到的海淀外,其余为化名)展开田野式书写叙述。地域不同、生存背景各异,这些家庭面临的困境却惊人地相似——许多父母在孩子彻底崩溃后才意识到严重性,有些父母甚至比孩子更早陷入心理危机。父母与孩子身处同一场风暴,以不同的方式承担着难以言说的代价。
我们和梁鸿教授进行了对话,这篇文章无意归咎于任何一方,而是希望呈现:在系统性压力下,休学家庭是如何一点点裂开,又应当怎样在破碎与错位中重新尝试理解彼此。

梁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抑郁家庭,是谁先病了
“他们也在苦海之中。”
——摘自《要有光》
2022年8月的一天,16岁的雅雅在家中突然崩溃。
那天,妈妈的朋友来探望,反复劝她“要坚强”“别太脆弱”。这些话像针一样扎进耳朵,她瞥见一旁默默流泪的妈妈,感到难以承受的绝望。下一秒,她冲进厨房拿起刀挥舞,并未伤人,却因此被送入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
这场崩溃早有预兆。就在四个月前,雅雅已被医生诊断为中度抑郁和中度焦虑,并开始服用抗抑郁药。但药效有限,她的情绪持续低落,整日昏昏欲睡,食欲减退。
更深层的压力,埋藏在她的成长轨迹里。雅雅从小是父母的骄傲,一路考进全市最好的中学。高一那年,她在班里的排名下滑,压力如潮水般涌来。最焦虑时,光是坐在教室里听同桌翻试卷、写字,她就浑身冒汗,满脑子都是:“她会不会超过我?”后来,一想到考试,她的手就控制不住地发抖。
雅雅生病后,家里的气氛变得沉重。“我找妈妈倾诉,她比我哭得还厉害;我沮丧,她比我更沮丧。”爸爸则更加失控,有次甚至跪在地上磕头哀求:“你快好起来吧,我们都受不了了。”

在家里感到痛苦的少女,《狗十三》剧照
雅雅开始看精神科的那一年,也正是梁鸿将目光投向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起点。作为一名写作者,也是一位海淀妈妈,她对这类议题有着天然的感知力。在与周围北京家长的交谈中,她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正被情绪问题困扰。
数据印证了她的观察。《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指出,在12至18岁的青少年中,24.6%出现了抑郁症状,其中7.4%为重度抑郁症。而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等群体的抑郁检出率更高。
梁鸿并非心理学家或社会学专业人士,她选择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靠近并记录下这些家庭的真实处境。她想追问:“在漫长的陪伴和养育过程中,我们究竟在哪些关键时刻错过了孩子?”
她在网络上发起信息征集,雅雅是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主动回应的孩子。访谈中,这位少女展现出的敏感与思考深度令梁鸿震撼,雅雅说:“如果我的故事能让别人看到,哪怕他们只能获得一点点信心,我也觉得值得。”
此后三年,梁鸿陆续又走访了数十个因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孩子的家庭。她发现,当孩子陷入心理危机时,本该成为支撑的父母,往往自身已经不堪重负。
这种困境不分地域或阶层。无论是大城市中产家庭,还是小城普通家庭,面对孩子的情绪问题,家长们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否认、回避,甚至在孩子面前率先崩溃。不少家庭都出现父母与孩子同时服用抗抑郁药的情况。

台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讲述家庭中扭曲的亲子关系
生活在北京的陈清画一家是典型的中产家庭。儿子吴用热爱数学,却厌恶机械的刷题训练。他从某一天开始拒绝上学,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陈清画不敢打扰,只能悄悄站在门外,屏息听着房间里的细微声响。有时孩子毫无回应,她便觉得整个世界成了灰色,茫然无措。
千里之外的一个县城里,杜梅的家庭同样深陷痛苦。她有两个孩子:女儿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儿子则患有精神分裂症。她自己严重失眠,靠药物勉强入睡,自己服药外,每天还要监督孩子们按时服药。女儿频繁拒绝上学,母女之间因此爆发一次次漫长而疲惫的争执。
对许多父母而言,孩子按下暂停键的那一刻,自己的人生仿佛也随之停滞。有人辞去工作,全天候陪护;有人奔波于医院、学校与家之间;还有人尝试转学、旅行,希望换个环境能带来转机。然而,家庭内部的紧张与冲突不断加剧。长期的压力与焦虑,已将他们的承受力推至临界点,崩溃只在一线之间。

妈妈们的困境
“她像经历了一场地震,过去所做的一切,成为妈妈的喜悦,为妈妈这个名头付出的努力、每一天的殚精竭虑,都被完全否定。”
——摘自《要有光》
但即便同为父母,面对孩子生病时的反应与承受的压力,女性与男性往往并不对等。
梁鸿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大多数孩子的冲突都是和母亲发生的,母亲好像成了迫害者。而这背后,是父亲的缺席。”
雅雅深陷情绪漩涡时,仍敏锐地感知到妈妈的崩溃。为了陪伴她,妈妈不得不频繁请假。每当看到她痛苦挣扎,妈妈束手无策,只能一遍遍无助地说:“让妈妈来替你吧。”

崩溃无助的妈妈,《小欢喜》剧照
爸爸在雅雅的记忆中始终是缺位的。从小,他很少关注她的情绪,也不了解她的内心世界。生病后,爸爸的反应更加极端:有时摔门而出,远远躲开哭泣的妻子和女儿,有时则把矛盾指向妻子,指责她“教育失败”,认定是她的过错导致了孩子的问题。
“在家庭内部,一种无意识的分工依然根深蒂固。”梁鸿分析道。尽管现代社会倡导性别平等,女性也早已走出家庭参与公共生活,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仍在悄然运作,育儿责任仍被默认为母亲的天职。
内蒙古大学发布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女性的总劳动时间远超男性,平均每天在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上投入超过3小时。其中就包括大量看不见却耗神的情感照料。
许多母亲不仅承受着孩子病情带来的巨大压力,深陷自责与无助之中,还要面对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二次伤害:“你是怎么带孩子的?”

图源:《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
丈夫的沉默和回避,进一步加重了她们的无助感。陈清画的儿子刚开始休学时,她常常在工位上控制不住地流泪,却不知该向谁倾诉。即便是最亲近的丈夫,每当她试图沟通孩子的近况,换来的往往是敷衍:“管他干什么”“我开会了”,随即挂断电话。
一次,夫妻俩一同去见家庭心理咨询师。咨询师提醒他们:“孩子出现问题,一定是家庭关系出了问题。”接着补充道:“即使家里没有暴力,也不能代表没有问题,相反,问题可能更隐蔽、更严重。”

全家一起接受心理咨询,图源:《小欢喜》剧照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陈清画的好友文莉身上。文莉一直信奉“快乐教育”,但儿子进入高中后逐渐拒绝上学,休学一年仍无复学迹象。她的丈夫是科研人员,专注学术,这曾是文莉欣赏他的原因。可婚后,他长期泡在实验室,对孩子的情绪变化毫无察觉。当问题爆发,他的第一反应是归咎于妻子对孩子成绩不上心,而孩子又过于娇惯自我。
文莉曾尝试推动改变,让丈夫更多参与孩子的生活。丈夫起初也答应了,下班回家做饭,陪孩子写作业,但父子间始终没有太多交流,几天后,他感到“孩子似乎并不需要我”,于是再次回到了实验室。
梁鸿指出,这并非指责所有父亲都不尽责,而是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家庭内部的结构与责任分配。父亲不只是经济支柱,还需要成为情感支持的一部分。唯有父母共同承担养育中的情绪劳动与陪伴,家庭才能形成合力,一起面对孩子成长中无法回避的困境。

被成功学捆绑的社会
“父母这一代才是‘空心病人’,能挣来钱,获得社会地位就非常满足。父母要的是功成名就,孩子想的是‘我为什么活着’。”
——摘自《要有光》
孩子究竟为什么病了?
梁鸿是七十年代生人。在她的成长记忆里,上学是改变命运的最佳路径。
而今天很大一部分孩子,物质条件远胜从前,却似乎被困在更狭窄的生存通道里。他们从小出入博物馆、游走于互联网,在信息洪流中早早看见世界的辽阔与多元;可一旦进入初高中,便被迅速塞进应试教育的“模具”,成绩成为唯一标尺,成功被简化为“好好读书、将来赚大钱”。
这种剧烈的割裂感,让许多思辨性更强、更敏感的孩子陷入困惑:如果世界如此丰富,为何我的人生只能有一条路?

丧失意义感,困扰着很多未成年和刚成年的年轻人,电影《大象席地而坐》
在梁鸿走访过的县城里,一位高中女孩在自杀前曾与班主任对话,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绝望。她成绩不理想,认定自己考不上大学。即使侥幸考上,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班主任以为这是考前焦虑,安慰她说:“只要能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好。”但几天后,女孩喝下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上学有什么意义?”或许是许多不愿返校的孩子内心最真实的叩问。
曾几何时,“努力读书、考上好大学、获得好工作”是一条被广泛信任的人生路径。但如今,这条路径的确定性正在被瓦解。尽管每年有数百万学生升入本科,能进入“双一流”高校的仍是极少数;即便手握名校文凭,也未必能换来体面安稳的工作。“好成绩等于好未来”的神话逐渐破裂,许多年轻人因此陷入深深的迷茫。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指出,这种困境源于一种名为“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社会逻辑:它将个人价值等同于才能、努力与成就,并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失败也归咎于自己。
“当人们相信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桑德尔写道,“那些天赋出众的年轻人反而承受着沉重的竞争压力,抑郁和焦虑成为普遍现象。”

《精英的傲慢》作者提到自己写书的初衷是为了激发更多人重新思考成功的意义
这种逻辑不仅塑造了孩子的自我认知,也深深绑架了父母。在北京海淀,陈清画、文莉等母亲曾在一次聚会中讨论:“如果当初让孩子上职高,是不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话音落下,一片沉默。在场的父母都是通过奋斗从外地考入北京、安家立业的一代人,曾是教育筛选中的“幸存者”,从未真正考虑过孩子向下流动的可能。
当一个人的价值被简化为成就,亲情也难免被异化。当儿子李风持续拒绝上学、对一切失去兴趣时,文莉对他产生了厌恶感:“我讨厌弱者,哪怕是我的儿子。”她清楚,孩子一定能感受到这份隐秘的失望。

这样的想法捆绑了孩子也捆绑了自己,《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剧照
否定不仅来自家庭。文莉曾带儿子去一家连锁快餐店应聘,店长得知他未满18岁且高中未毕业,直接拒绝:“一是未成年,二是这里不是接收站,谁来都可以。”那一刻,她意识到:即使是陌生人,也在用同一套标准审判她的孩子。
事实上,在成功学主导的逻辑里,没有真正的赢家。无论“胜出”还是“淘汰”,所有人都在为一个虚幻的标准付出代价。
正如一位豆瓣读者在书评中写道:“如果读完这本书只觉得‘有的父母不配当父母’,那其实挺遗憾的。书中呈现的是结构性问题——人被工具化,家长何尝不是在承受痛苦?”
梁鸿认为,唯有打破对成功的单一想象,才能真正解放两代人。当长期的学业压力已让孩子身心俱疲,父母或许可以尝试接受另一种可能:“孩子能在某个领域投入热情,哪怕未来月入三千,未必不是一种成功。”

在破碎和错位中相互理解
“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复杂性和必然性。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文明的创伤,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并不是可疗愈的东西。”
——摘自《要有光》
在漫长的痛苦与反复中,一些父母开始照望自身,也重新审视与孩子的关系。
雅雅妈妈意识到,这些年她几乎把全部生活都绕着女儿打转,看似无私,实则给孩子施压,她从未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那份窒息感。后来,她试着把生活重心移回自己身上:去逛街、看电影、读书,练习做一个不靠牺牲来证明爱的母亲。
陈清画也在追问自己:“为什么没能更早看见孩子的痛?”她曾以为送儿子进双语幼儿园、报兴趣班,就是托举他的未来,却未察觉,那些精心安排也可能成为枷锁。即便她口头认同“刷题伤害思维”,行动上仍不断催促孩子多做几道题,不知不觉,站到了孩子的对立面。
还有一位农村母亲,生计已捉襟见肘,却仍在读心理学书籍,只盼能借此读懂孩子的心,陪他走出深渊。
但改变并不容易。开补习班的阿叔曾对梁鸿说:“很多家长冥顽不化,与其指望他们改变,不如直接帮孩子。”起初她觉得这话太绝对,但在走访数十个家庭后,不得不承认:许多父母确实困在自己的认知牢笼里,难以挣脱。
雅雅也深知这一点,她认为父母很难真正改变。但冷静下来,又能看到更深的根源:“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精神上给我爸妈的都不是很好的东西,这导致他们会用在我身上。”
“创伤是一种必然。”梁鸿在采访中说道。她指出,每个人都是带着某种创伤生活,它可能来自家庭、教育、成长环境,一代代人承袭着相似的话语、习惯与期待,把未被疗愈的痛,误当作爱传递下去。
但她也强调,觉察是改变的开始。即使无法彻底疗愈自己,父母至少可以学会辨析:不再理所当然地将未曾解决的创伤,复刻到下一代身上。
于是,她将书命名为《要有光》——那束光,不只为照亮孩子,更要照亮整个家庭幽暗的角落。

梁鸿新书《要有光》
书出版后,有读者开始思考:能否在问题爆发前,就看到亲子关系中那些长期积累的错位?这让梁鸿感到欣慰,哪怕只是细微的改变,也意味着光照进了一些地方。
但她也清醒地知道,现实依然残酷:休学家庭普遍缺乏社会支持。精神困境不像发烧或骨折,没有清晰的诊疗路径。“孩子看起来好好的,为什么病了?”“到底该不该吃药?”面对这些困惑,父母们常常得不到确切答案,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本着最朴素的心来写下这些故事,我看到了,我琢磨了,尽全力把这种复杂性呈现出来,这就完成了第一步。”她说。

梁鸿
在书的后记中,梁鸿称,自己的目的从来不是控诉家庭、教育体系或是社会系统,而是试图捕捉藏在日常话语和行为里的细小节点,正是这些微妙的瞬间,悄然改变了一个孩子、一段关系,甚至决定了事情何时发生质变。
她始终记得一个孩子对她说的话:
“没有一个整全、美好的家庭概念。创伤是生命的本质存在形式。我们必须学会在创伤中往前走,在一种必然的破碎中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