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僖宗光启年间,长安城的暮色总带着几分凄惶。战乱的阴影已悄然笼罩着这座曾经繁华的帝都,街头巷尾,流浪乞讨者渐增,百姓的脸上写满不安。
在这些流浪者中,有一个姓郎的男子,无人知晓他从何处来,也无人问津他将往何处去。郎姓男子约莫三十来岁,面容枯黄,衣衫褴褛,每日只在护城河边游荡,捡拾些残羹剩饭度日。长安城虽大,却没有他立锥之地。
此时朝中,宦官田令孜权倾朝野。唐僖宗十二岁登基,尚是孩童,朝政大事皆由这位“阿父”田令孜把持。田令孜虽为阉人,却极爱排场,出行必是八抬大轿,前呼后拥,气派非凡。
一日春末,护城河边杨柳依依,桃花正盛。田令孜乘轿路过,见景致宜人,便吩咐停轿,欲漫步赏春。他身着紫色官袍,腰佩金鱼袋,左右侍从十余,所到之处,行人纷纷退避。
田令孜沿河缓行,欣赏着这难得的春光。行了约百步,忽觉腿脚酸软——前日宫中议事至深夜,今日又早早起身,确实有些倦了。他四顾寻觅,想找个地方歇脚,却见这河岸整洁,竟无一处可坐。
正犹豫间,忽见一人趋步上前,伏地跪拜:“小人愿为大人效劳。”来人正是那姓郎的流浪汉。他双膝跪地,双手撑地,躬身如凳,恭敬异常。
田令孜微微一愣,随即明白此人是要以身作凳。他心中大奇,却不露声色,从容坐下。那郎姓男子身形虽瘦,背脊却挺得笔直,竟也十分稳当。
田令孜坐了约一盏茶的功夫,起身时心情大好,笑道:“你这人倒也有趣,姓甚名谁?何方人士?”
郎姓男子连忙再拜:“小人姓郎,贱名不足挂齿。原是陕州人士,家道中落,流落至此。”
“可曾读过书?识得字?”
“小人略识几个字,读过些诗书。”郎姓男子小心翼翼地回答。
田令孜仔细打量眼前这人,见他虽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眉目间却透着一股机敏,言谈举止也不似寻常流浪汉粗鄙。更难得的是这份察言观色、曲意逢迎的本事,在这落魄之时仍能如此,实非常人。
“你既无家可归,可愿随我回府?”田令孜问道。
郎姓男子闻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连叩首:“愿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自此,长安城中少了一个无名流浪汉,田令孜府中多了一个贴身侍从。郎姓男子极善揣摩主人心意,又口齿伶俐,不出数月,便成了田令孜跟前红人。田令孜赐他名“郎仲平”,取中庸平和之意,又提拔他担任左军使,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一跃成为从六品官员。
郎仲平对田令孜的恩情感激涕零,伺候得越发周到。他深知自己的一切皆系于田令孜一身,故而对这位权倾朝野的“阿父”忠心不二,凡事唯命是从。
一日朝会,唐僖宗问起北方藩镇事宜:“河东节度使空缺已有月余,爱卿以为何人可任此职?”
田令孜略一沉吟,便道:“陛下,臣以为左军使郎仲平忠勇可嘉,可担此重任。”
僖宗年幼,对田令孜言听计从,当即准奏。诏书下达那日,郎仲平捧着那卷黄绫文书,双手颤抖不已。河东节度使!那可是统辖数州军政大权的一方诸侯,是多少官员梦寐以求的封疆大吏之位!
当晚,郎府张灯结彩,宴请宾客。郎仲平多喝了几杯,满面红光,频频举杯。席间宾客纷纷祝贺,谀词如潮,郎仲平飘飘然,仿佛已置身于河东帅府,手握重兵,威风八面。
然而乐极生悲。深夜宴散,郎仲平回房歇息,睡到半夜,忽觉心口一阵剧痛,冷汗涔涔而下。家人慌忙请来太医,却已是回天乏术。
弥留之际,郎仲平唤来独子郎权贯。那年郎权贯刚满十八,面容清秀,颇有几分其父年轻时的影子。
“儿啊,”郎仲平气若游丝,“为父幸得田令孜大人提携,方有今日。如今诏命已下,我却无福消受...我死之后,你速去田大人府上哭诉,他念及旧情,或能庇护于你。”
郎权贯含泪点头。
郎仲平喘息片刻,又道:“无论将来如何,切记要善意待人...万事不可做绝,定要留有余地...这是为父用一生...悟出的道理...”
话未尽,人已逝。
郎权贯依父嘱,披麻戴孝前往田府报丧。田令孜闻讯,倒也真有几分伤感,见郎权贯哭得悲切,又念及其父多年侍奉之功,便道:“你父亲忠心耿耿,不料竟如此福薄。你既是他独子,便由你承袭父职,往河东赴任吧。”
于是,年方十八的郎权贯,一夜之间成了河东节度使,统领数州军事民政。少年得志,春风得意,自长安赴任途中,沿途州县官员无不夹道迎送,极尽奉承。
起初几年,郎权贯尚记得父亲临终教诲,处事谨慎,待人尚有几分宽容。然权力如美酒,日久便醉人。尤其当黄巢起义军势如破竹,唐僖宗仓皇逃往成都,田令孜召郎权贯率兵护驾之后,情况便大不同了。
在成都,田令孜大权独揽,而作为田令孜心腹的郎权贯,自然水涨船高。那些求官者、谋差者、想逃避罪责者,如过江之鲫,携重金厚礼登门拜访。起初郎权贯尚能推拒一二,后来便习以为常,再后来竟索要无度。
不过五年光景,郎权贯已敛财千万,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府邸奢华堪比王侯。门前车马日夜不绝,府内歌舞通宵达旦。他渐渐变了,变得骄横,变得贪婪,变得目中无人。
一日,一位昔日同僚之子前来求助。其父因开罪权贵被贬,想请郎权贯在田令孜面前美言几句。那青年家境已败落,只能凑出百两银子作为谢礼。
郎权贯斜眼看了看那包银子,嗤笑道:“百两银子就想办这样的事?你当我是叫花子不成?”
青年满面通红,恳求道:“郎大人,家父曾与令尊有旧,望大人念在昔日情分...”
“情分?”郎权贯打断他,“情分值几个钱?没有三千两,免谈!”
青年含泪而去。郎权贯的母亲在屏风后听见,待客散后,将儿子唤到跟前。
“贯儿,”郎母语重心长,“你如今权倾一时,但需知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凡事不可做绝,能帮人处且帮人,给自己留条后路才是。”
郎权贯不以为然:“母亲多虑了。如今田大人权倾朝野,我就是田大人最信任的人,能有什么难处?”
“可田大人的权势,难道就能永固不成?”郎母忧心忡忡。
郎权贯哈哈大笑:“母亲真是妇人之见!这天下,谁能动得了田大人?”
话音未落,门外忽有急报送来:西川节度使王建以“清君侧”为名,率大军已逼近成都!
原来田令孜专权多年,早已引起诸多节度使不满。王建便是其中之一,他联合数镇兵马,直扑成都,声称要诛杀奸宦,还政于天子。
消息传开,成都大乱。田令孜慌忙挟持唐僖宗准备再次出逃,却已来不及。王建大军如潮水般涌入成都,田府首当其冲。
那夜火光冲天,喊杀声四起。郎权贯从睡梦中惊醒,只披一件外袍,赤脚逃出府邸。他回头望时,自家府宅已陷入火海,妻妾儿女的哭喊声渐次消失于刀剑碰撞声中。
他混入逃难人群,仓皇出城,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昔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一夜之间成了丧家之犬,除了一身单衣,别无长物。
郎权贯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他先是想投奔昔日那些受过他“恩惠”的官员,可每到一处,不是被拒之门外,就是遭人白眼。有一次,他甚至被一个曾跪求他办事的小吏放狗追咬。
“滚!你这田令孜的走狗!还敢来见我?”那小吏站在门前怒骂,“当年我老母病重,求你借十两银子救命,你却要我五百两的‘手续费’!我母亲就是那时死的!滚!再不滚我打死你!”
郎权贯抱头鼠窜。他这才想起,这人的确曾来求过他,那时他嫌礼薄,故意刁难,哪想到今日...
时值深秋,寒风刺骨。郎权贯衣不蔽体,腹中饥饿,只得沿途乞讨。可他那身破烂官袍虽已污秽不堪,仍能看出曾经的华贵质地,百姓见了,不是躲得远远的,就是冷嘲热讽:
“哟,这不是那位‘郎仆射’吗?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了?”
“活该!当年我叔叔不过想谋个书吏的差事,他开口就要二百两!我叔叔凑不出,回家气得一病不起!”
“听说他府上抄出千万家财,都是民脂民膏啊!”
郎权贯低头疾走,满脸羞惭。他终于明白母亲那句“花无百日红”的含义,也终于懂得父亲临终那句“留有余地”的深意,可惜为时已晚。
辗转月余,郎权贯来到复州地界。此时他已形同乞丐,蓬头垢面,脚上满是血泡。一日,他饿得头晕眼花,倒在路边,几近昏迷。
朦胧中,忽听有人唤他:“郎...郎公子?”
郎权贯勉强睁眼,见一中年男子蹲在他面前,面庞黝黑,双手粗糙,似是军中士卒。
“你是...”郎权贯声音嘶哑。
“小人是颜老三啊!当年在您父亲手下喂马的!”那人激动道,“您怎么...怎么落到这般境地?”
郎权贯羞愧难当,欲言又止。颜老三却不由分说,将他扶起,背回家中。
颜老三家徒四壁,只有两间茅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他煮了热粥,端给郎权贯,叹道:“当年我丢失战马,按律当斩,是您父亲力保,免我一死,只调来复州养马。这恩情,我一辈子记得。”
郎权贯喝着热粥,泪水滚滚而下。他想起来了,父亲在世时,的确常行善事,救助过不少人。可自己得势后,却将父亲这最宝贵的遗训抛之脑后。
颜老三无妻无子,独自一人生活。他让郎权贯住下,对外只说这是远房侄子。郎权贯感激涕零,改名“颜思昔”,取“思念往昔”之意,也暗含悔过之心。
过了大半年,颜老三忽染重病,卧床不起。军中养马的差事眼看就要丢了,一家生计将无着落。颜思昔思虑再三,对颜老三道:“义父,让我去顶替您养马吧。”
颜老三摇头:“你曾是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怎能做这等卑贱之事?”
颜思昔苦笑:“如今的颜思昔,不过是个乞儿。若非义父收留,早已冻死饿死。养马虽贱,却是正经生计,能报答义父恩情于万一,我心甘情愿。”
颜老三见他意诚,只得应允。于是,曾经的节度使郎权贯,成了复州军营中一名养马军士。
养马虽苦,颜思昔却做得认真。他每日天不亮就起身,铡草、拌料、刷洗马匹,忙到日落方休。军营中有些人知道他的底细,常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看见没?那个新来的养马的,听说以前是节度使呢!”
“什么节度使,不过是田令孜的一条狗罢了!”
“活该!这种人也有今天!”
颜思昔听见,只低头做事,不发一言。偶尔有年轻气盛的军士当面嘲讽:“喂马的仆射大人,这马粪香不香啊?”他也只笑笑,继续清扫马厩。
唯有夜深人静时,他才会望着星空,想起昔日的荣华富贵,想起父亲临终的教诲,想起母亲担忧的面容,想起那些被他羞辱、被他勒索的人...泪水无声滑落。
如此过了三年。一日,军营中忽然骚动起来,说是朝廷派了新的观察使前来巡查。颜思昔本不在意,依旧在马厩忙碌。
午时,忽有军吏来唤:“颜思昔,观察使大人传你问话!”
颜思昔心中一紧,不知祸福,只得整了整破旧军服,随军吏前去。
中军帐内,一位四十余岁的官员端坐案后,面庞方正,目光如炬。颜思昔跪下行礼,不敢抬头。
“抬起头来。”观察使声音平和。
颜思昔缓缓抬头,与观察使四目相对,两人都愣住了。
这观察使,竟是当年那个携百两银子为父求情,却遭郎权贯羞辱赶出的青年!
观察使盯着颜思昔看了许久,帐中一片寂静,只闻帐外风声。军吏们面面相觑,不知这位新任观察使为何独召一个养马军士问话,又为何如此长时间沉默。
颜思昔心跳如鼓,额上渗出细密汗珠。他认出眼前人时,脑中一片空白,只觉天旋地转。完了,他想,终究是逃不过。这三年平静的日子,怕是要到头了。他闭上眼,等待雷霆之怒降临。
不料观察使却缓缓开口:“你...就是颜思昔?”
“是...小人正是。”颜思昔声音颤抖。
“在军中养马几年了?”
“三...三年有余。”
观察使点点头,又沉默片刻,忽然对左右道:“你们都退下。”
帐中只剩二人。观察使起身,走到颜思昔面前,俯视着这个跪在地上、浑身颤抖的养马人。良久,他轻叹一声:“你可知我是谁?”
“小人...小人知道。”颜思昔伏地不敢起,“当年小人糊涂,对大人多有得罪...今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只求莫要连累颜老三,他是无辜的。”
观察使却不接话,反而问道:“你这三年,可曾想过当年之事?”
颜思昔泪如雨下:“日日思,夜夜想。每念及当年所作所为,悔恨交加,恨不能以死谢罪。小人不求大人原谅,只求...”
“只求什么?”
“只求大人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颜思昔叩首道,“小人愿为大人做牛做马,弥补万一。”
观察使负手踱步,帐中只闻脚步声与颜思昔压抑的抽泣声。终于,他停下脚步,沉声道:“当年我父亲被贬,我携百两银子求你,你拒之门外。我归家后三月,父亲郁郁而终。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儿啊,莫要怨恨。权势如烟云,今日他盛,明日或许就衰。你记住,无论将来如何,待人须留余地。’”
颜思昔闻言,如遭雷击。这句话,与他父亲临终所言何其相似!
观察使继续道:“我牢记父训,寒窗苦读,侥幸中举,一步步走到今日。这一路上,我时刻告诫自己:得志时莫猖狂,失意时莫颓丧。待人宽一分,便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他转身看着颜思昔:“你这三年养马,勤勉踏实,军中上下有目共睹。那些曾受过你欺压的人来复州公干,你也避而不见,不愿再生事端。这些,我都知道。”
颜思昔惊愕抬头。
“我今日见你,本有两念。”观察使目光复杂,“一为私怨,恨你当年势利,致我父早逝;二为公心,念你这三年洗心革面,踏实做人。”
他顿了顿:“我父临终教诲,与令尊所言,如出一辙。可见这世上道理,本不分贵贱,只分悟与不悟。你悟了,虽晚,但终是悟了。”
颜思昔痛哭失声:“小人...小人愧对先父教诲...”
观察使扶起他:“从今日起,你不在马厩做事了。我调你来帐中做文书,你可愿意?”
颜思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人...您不追究...”
“往事已矣。”观察使摆摆手,“我父若在天有灵,也不愿我挟怨报复。你既已悔过,我便给你一个机会。只是切记,此次机会,是令尊的遗泽所荫,是颜老三的善心所报,也是你自己这三年的改过所换。望你珍之重之。”
颜思昔跪地长拜,泣不成声。
自此,颜思昔在观察使帐下做文书,兢兢业业,谦逊谨慎。他常将所得俸禄分与军中贫苦士卒,又出资在复州设义塾,供穷苦子弟读书。有人问起他的过去,他只笑笑:“昔日种种,譬如昨日死。”
数年后,观察使升迁离任,临行前问颜思昔可愿随行。颜思昔婉拒:“小人余生,愿在复州侍奉义父终老。”
观察使颔首:“善。”
颜思昔送别观察使那日,秋风萧瑟,黄叶纷飞。他站在复州城头,望着远去的车马,想起这半生浮沉,恍如一梦。
颜老三于次年春天安详离世,颜思昔守孝三年,后在复州城外结庐而居,以抄书授徒为生。他常对学子们说:“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为人处世,当如江河,虽奔腾向前,却总为支流留余地。”
有好奇者打听他的身世,他只笑而不答。唯夜深人静时,他会取出父亲留下的那枚旧玉佩,摩挲良久,轻声吟诵杜牧的《金谷园》: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吟罢,望着窗外明月,喃喃自语:“父亲,您的教诲,儿终于懂了。”
复州城的百姓只知这位颜先生是个有学问的善人,却不知他曾经是权倾一时的郎仆射。那些往事,随风而散,只有护城河边的杨柳,岁岁枯荣,见证着人间的兴衰荣辱。
而“留有余地”四字,成了颜思昔余生恪守的信条,也成了他传授给弟子们最宝贵的道理。这道理简单,却需用半生浮沉方能真正领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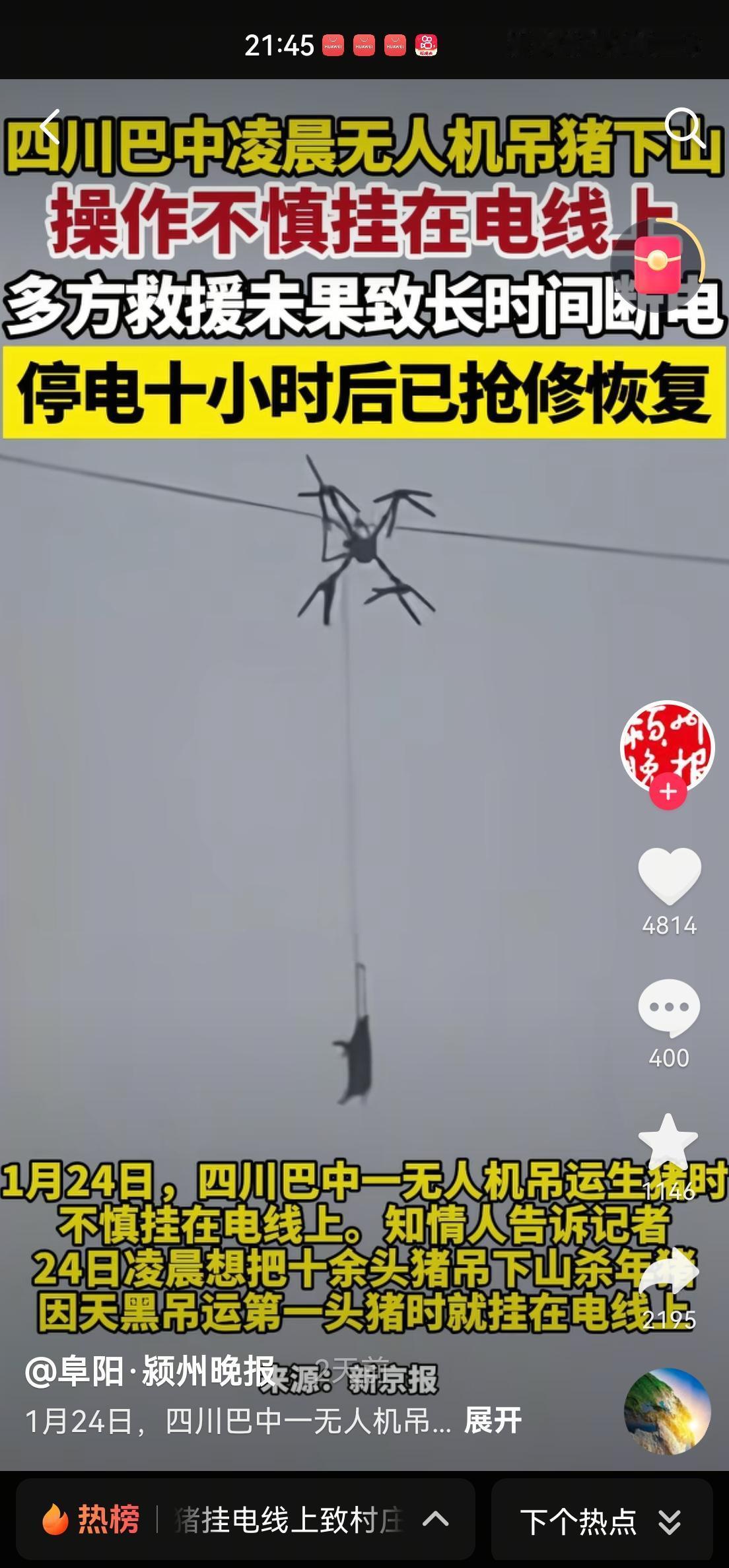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