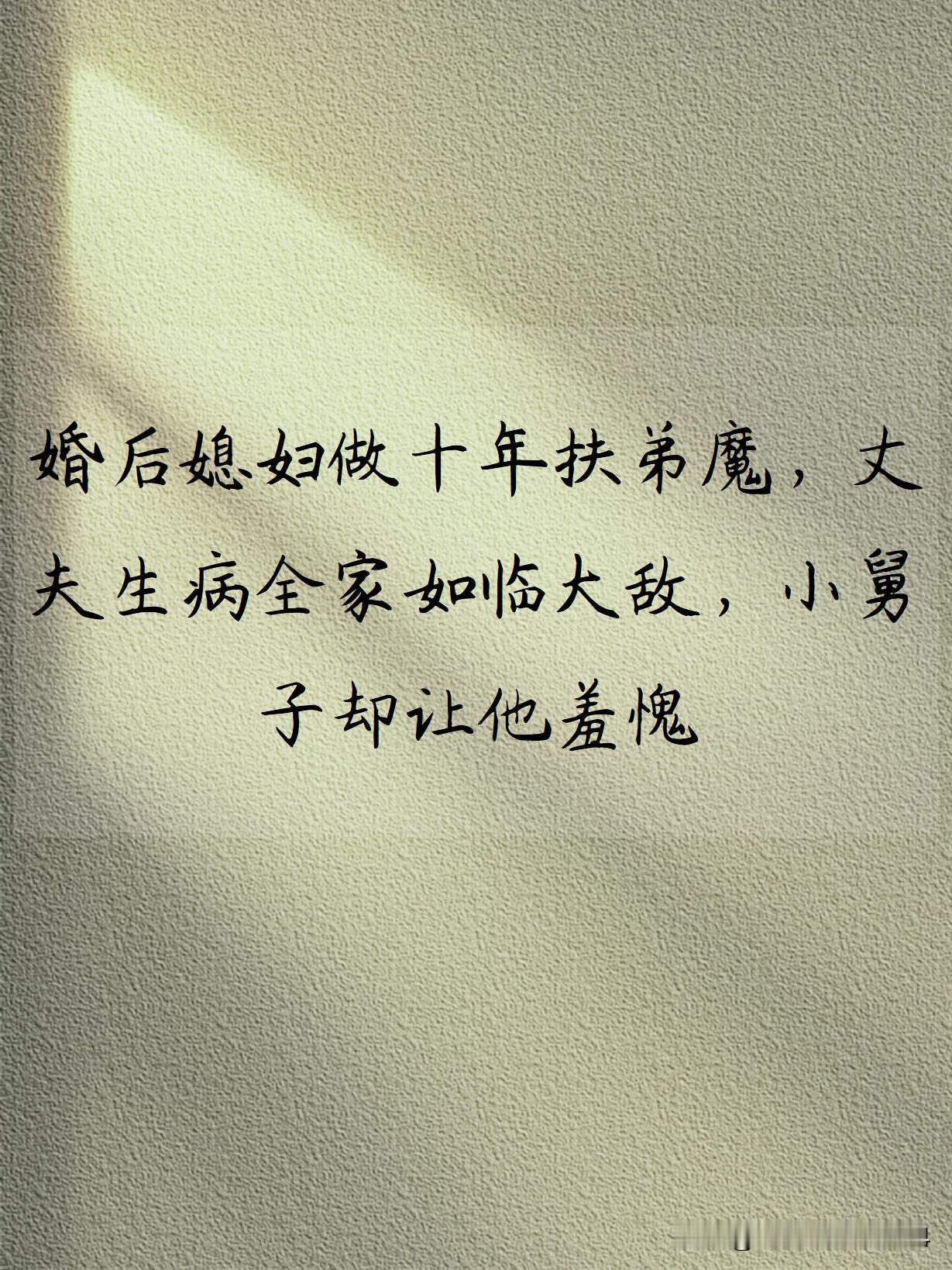宫里有个规矩,三更锣响,焚尸炉无论有什么动静都不能开。
炉子里烧的,是中了蛊的宫女,或是怀了鬼胎的娘娘。
我是焚尸所的守夜人,在这里活得最久。我不问缘由,只管烧火。直到建元七年那个雨夜,大内总管亲自押来一口楠木棺材,棺材缝里渗着血,贴着明黄封条——九族皆杀的重罪标记。
总管太监把一锭金子塞进我怀里,那手凉得像蛇信子,贴着我耳边说了一句阴森的话:“今晚这炉火得烧旺点,万岁爷说了,连这孽种的骨灰,都不能留下一粒。”
等他们走后,我准备起火,那钉死的棺材盖里,竟传出婴儿的啼哭,还有女人指甲抓挠木板的刺耳声响……
01
那哭声刺进我耳膜,我手一抖,火折子差点掉在地上。
“听见什么了吗?”
那个阴恻恻的声音又在身后响起。
我后背的汗毛瞬间立了起来。大内总管海公公没走,他站在阴影里,一双浑浊的眼珠子死死盯着我的脖子,手里捏着块帕子,上面有股刺鼻的杏仁味——是用来捂死人的毒药。
他在试探我。
他想知道我会不会好奇开棺,又或者有没有听出棺材里的不对劲。
我立刻弯腰,用满是烧伤疤痕的手指挖了挖耳朵,装作什么也没听见,憨傻的把那锭金子放进嘴里咬了一口,露出一口黄牙,嘿嘿傻笑:“谢公公赏!这金子软,成色足!够我买十坛烧刀子了!”
海公公盯着我看了会儿,那目光像毒蛇爬过我的皮肤,湿冷黏腻。半晌,他才用帕子捂住口鼻,嫌恶的往后退了一步:“果然是个只认钱的聋瞎子。烧干净点,要是明天早上咱家看到炉灰里还有一块骨头渣子,就把你也塞进去。”
“公公放心,火旺着呢。”我依旧点头哈腰。
脚步声终于远去,消失在哗啦啦的雨声里。
我脸上的傻笑瞬间消失,神情森寒。我快步走到大门前,透过门缝确认那些禁军确实撤到了百步之外,这才转身看向那口楠木棺材。
炉膛的火苗刚舔上棺材底,里面的动静突然变大了。
“咚!咚!咚!”
里面的人在用头撞击棺盖!
这棺材用的是七寸长的棺材钉,没有斧子根本撬不开。而且,就算撬开了又怎样?救一个注定要死的宫妃?
我在这冷宫待了十年,烧过无数没断气的尸体,早就练出了一副铁石心肠。我不想死,只想活着。
我深吸一口气,抓起一把松香就要往炉膛里撒,就在这时,棺材缝里传出一个虚弱的声音,却让我浑身一震:
“救我……修罗刀……我知道是你……”
我手中的松香洒了一地。
修罗刀。
这个名字,我已经整整十年没听过了。那是江湖上早已销声匿迹的头号杀手,是朝廷悬赏十万两黄金的恶鬼。
世上知道我是修罗刀的人只有三个。两个已经成了我的刀下鬼,还有一个……应该坐在龙椅上。
这棺材里的女人,到底是谁?
02
一瞬间,杀心在我胸膛里翻腾。
如果她知道我的身份,那她必须死。这把火,无论如何都得烧下去。
我的手却不听使唤,抄起了角落里的撬棍。那一声“修罗刀”喊得太过绝望,像一把钩子,硬生生勾起了我埋在骨子里的旧事。
“咔嚓——”
棺材钉被我硬生生撬起,楠木板发出令人牙酸的断裂声。
棺盖掀开的刹那,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混合着龙涎香扑面而来。
我举着油灯探头看去,瞳孔一缩。
躺在里面的女人衣衫破碎,华贵的云锦宫装被血浸透,紧紧贴在身上。刺眼的是她高高隆起的腹部——那根本不是什么鬼胎,是足足八个月的身孕!
她满脸是血,指甲全部翻裂,鲜血淋漓。借着昏暗的火光,我看清了那张脸。
荣贵妃。
当今圣上宠爱的女人,据说连冷宫的蚂蚁都不敢爬过她的绣鞋,此刻却像条死狗一样被扔在这个充满尸臭的焚尸炉前。
她大口喘息着,那双曾被诗人称颂的桃花眼死死盯着我,里面没有恐惧,而是一种疯狂的赌徒神色。
“我就知道……你躲在这……”她声音嘶哑,每说一个字嘴里都在往外冒血沫,“你不敢……杀我。”
我握紧手里的撬棍,尖端对准她的咽喉:“娘娘认错人了。奴才是烧火的,不知道什么修罗刀。”
“别装了……”荣贵妃突然伸手,死死抓住我的脚踝,力道大得惊人,指甲甚至掐进了我的肉里,“你能瞒过海大富,瞒不过我。你手背上的那道疤,是建元三年……替皇上挡的那一剑留下的。”
我眼神一冷,这女人知道得太多了。
“你想死个痛快?”我的声音冷了下来,不再掩饰。
“我想活……这孩子也想活……”荣贵妃痛苦的痉挛了一下,身下的血流得更凶了,她咬着牙,惨笑道,“你以为皇帝为什么要杀我?因为这孩子……根本不是他的!”
我皱眉:“宫闱丑事,我不感兴趣。”
“若是这丑事……能要了皇帝的命呢?”
荣贵妃猛地抬头,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的说出了那个能让整个王朝倾覆的秘密:
“狗皇帝三年前练功走火入魔,早就绝了后!这两年宫里生下的皇子,全都是借种!而我肚子里这个……他必须死,因为这个孩子的亲爹,是一条潜伏在他身边、随时能咬断他喉咙的恶龙!”
03
我的手腕一僵,撬棍悬在她喉咙上方三寸,却怎么也刺不下去。
借种?绝后?
这消息要是传出去,今晚别说焚尸所,整个皇宫都得血流成河。
“所以,你也是借的种?”我看着她高隆的肚子,心里一阵恶心,“既然是借种,生下来便是皇子,为何要杀你?”
荣贵妃惨白着脸,突然从怀里颤巍巍的掏出一件东西,举到我面前:“因为……我没能把这东西处理干净。”
那是一块玉佩。
一块染了血、缺了一角的青玉麒麟佩。
看清那块玉佩的瞬间,我脑子“嗡”的一声,像是被人敲了一闷棍。所有血液倒流回心脏,撞得我胸口剧痛。
那是我的家传玉佩。
十个月前,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早已隐退的我接到密旨,皇帝在御书房召见我,说是叙旧,赐了一壶“醉仙酿”。
我记得那酒很烈,喝下去浑身燥热,意识逐渐模糊。我记得皇帝拍着我的肩膀说:“爱卿体魄强健,乃是我大梁的脊梁。”
再醒来时,我躺在冷宫的枯井边,衣衫整齐,除了头痛欲裂,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只是那块从不离身的麒麟佩不见了。我以为是落在了御书房,根本不敢去问。
现在,它出现在荣贵妃的手里。
出现在一个怀胎八月的女人手里。
“想起来了吗?”荣贵妃看着我僵硬的脸,眼泪混着血水滑落,“那晚那个蒙着眼、被喂了药扔进我偏殿的男人……就是你。”
“不可能!”我下意识的低吼,往后退了一步,撞在滚烫的炉壁上,“我是太监!我是焚尸匠!”
“你是先帝的影子护卫,你是没有净身的假太监!这事儿只有皇上知道!”荣贵妃凄厉的喊道,随后痛苦的捂住肚子,“那晚……我也是被灌了药的……我不知道是你……直到事后我看见了这块玉佩……”
轰隆——
窗外一道惊雷炸响,惨白的电光照亮了这间阴森的焚尸房。
我浑身冰冷,手指剧烈颤抖。
我以为我隐姓埋名是在苟活,原来在皇帝眼里,我不过是一头种猪!用完了,还要把我千刀万剐,连我的骨肉都要烧成灰!
血液冲上头顶,我这十年的伪装瞬间崩裂。
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沉重的脚步声,不止两个人,是几十个穿着铁甲的禁军。
“吱呀——”
焚尸所那扇沉重的木门被人从外面猛地推开一条缝。
海公公那特有的公鸭嗓在风雨声中显得格外刺耳,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守夜的,怎么没听见烧尸的噼啪声啊?火灭了?还是说……里面的东西,跑出来了?”
04
那一瞬间,空气凝固了。
荣贵妃闭上了眼,而我,听到了自己血液奔涌的咆哮声。
大门被彻底撞开,火把的光亮瞬间刺破黑暗。海公公站在最前面,身后是两排手持强弩的禁军,黑洞洞的箭头在火光下闪着寒芒,直指我的眉心。
他看了一眼撬开的棺材,又看了一眼没烧起来的炉膛,那张老脸瞬间扭曲成一个狰狞的笑容:“咱家就知道,你这只老鼠藏不住骚味。果然是同党!”
他没有废话审问,直接下令灭口:“放箭!把这对狗男女射成刺猬!”
“崩!崩!崩!”
弓弦震动的声音连成一片,密集的箭雨像蝗虫一样扑来。
荣贵妃发出了绝望的尖叫。
在第一支箭射出的刹那,我动了。
我挺直了佝偻十年的后背。我脚尖挑起地上沉重的棺材盖,手腕一抖,那数百斤重的楠木板像纸片一样飞起,横挡在我们面前。
“笃笃笃笃!”
箭矢如暴雨般钉在棺材盖上,入木三分。
“什么?!”海公公尖叫出声,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就在这一瞬的间隙,我从腰间抽出那把用来铲煤的黑铁铲。这十年来,我没摸过刀,但这把铲子,被我磨得比刀还快。
我从棺材盖后冲了出去。
第一铲,削断了最前面那个禁军持弩的手臂。断肢飞起,鲜血喷溅在炉火上,发出“滋啦”的声响。
第二铲,拍碎了第二个禁军的喉骨。
我的动作快得像一道黑色闪电,在狭窄的焚尸房里,这些拿着长兵器的禁军反而成了活靶子。每一铲下去,都伴随着骨骼碎裂的脆响。
这是“修罗刀法”的起手式——鬼门关。
海公公吓得连退三步,一屁股跌坐在地,指着我哆哆嗦嗦的喊:“这身法……你是先帝身边的那个……”
“我是你祖宗!”
我一声暴喝,手中的铁铲旋转着飞出,在空中划过一道黑色的弧线,直接切开了海公公的喉咙。
他的话还没说完,脑袋就歪在一边,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里满是惊恐。
剩下的禁军乱了阵脚,我反手拔出海公公尸体上的佩刀。刀锋在手,一种久违的杀戮本能瞬间回归。
杀!
一刀一个,血水混着雨水流满了一地。
当最后一个禁军倒下时,焚尸房里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我浑身是血,转过身看向荣贵妃。
她脸色惨白如纸,身下一滩羊水混着血水正在迅速扩散。
“啊——”她痛苦的仰起头,双手死死抓着地面,“孩子……孩子要出来了……”
宫外,更多的脚步声正在逼近。震天的喊杀声说明刚才的动静已经惊动了整个大内侍卫营。
三千禁军,哪怕我是修罗刀再世,也不可能带着一个临产的女人杀出去。
我冲过去,一把将她背在背上,扯下布条把她和我的身体死死绑在一起。
“抓紧我!”我咬着牙,眼底一片赤红,“老子带你们娘俩杀出去!”
“别……别往宫外跑……”荣贵妃在我耳边气若游丝,指甲几乎陷进我的肩膀里,她说出了那个让我头皮发麻的生路,“宫外全是死路……唯一的活路在……皇帝的寝宫!去乾清宫!”
05
暴雨掩盖了踪迹,也让前路变得像沼泽一样难行。
荣贵妃在我背上烫得像个火炉,每一次宫缩,她的身体都会猛地绷紧,指甲透过湿透的衣衫掐进我的肉里。我不敢停,也不能停。
“到了……就是那个……红木柜子……”她在颠簸中气喘吁吁的指路。
这里是乾清宫的偏殿,皇帝平日里用来“修仙炼丹”的禁地。最危险的地方确实最安全,谁能想到,两个亡命徒敢躲进老虎的喉咙里?
我单手托着她,另一只手摸索到柜子后的机关——一盏不起眼的铜鹤灯。用力一旋,沉重的墙壁无声滑开,一股浓烈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
不是丹药香,是硫磺、水银,还有肉类在高温下腐烂的甜腥味。
我背着她闪身而入,反手合上机关。密室里点着鲛人油做的长明灯,光线昏黄摇曳。当我看清四周的景象时,饶是我这种杀人如麻的屠夫,胃里也忍不住一阵翻涌。
墙边架子上,摆满了一排排琉璃罐。
罐子里泡着的,是婴儿。
有的只有巴掌大,尚未成型;有的已经足月,却长着两个头,或是四肢扭曲成诡异的角度。这些都是皇帝为了求长生,试药失败后的“废料”。
“放我……下来……”荣贵妃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她的裙摆下,血水滴滴答答落在青砖地上,汇成一滩触目惊心的红。
我把她放在一张铺满药渣的石台上。她死死咬着一块手帕,因为剧痛,整张脸扭曲得如同厉鬼,脖颈上的青筋暴起,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隔着一堵墙,外面全是禁军的脚步声和铠甲碰撞的哗啦声。
“用力。”我跪在她两腿之间,双手沾满了她黏腻温热的血。我是个杀手,我知道怎么把人的肠子掏出来,却从不知道怎么把孩子弄出来。
“嗯——!”她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哼,眼珠上翻,几乎要晕厥过去。
“看着我!”我低吼道,用满是血污的手拍了拍她的脸,“别睡!你想让这孩子变成罐子里的那种东西吗?”
她猛地睁开眼,那是母兽护崽时的凶光。
“头……头出来了……”我感觉手心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一团,那是带着胎脂和血水的头顶。
就在这时,那面刚刚合上的机关墙,突然传来“咔哒”一声轻响。
是机括转动的声音。
有人进来了。
06
我的手瞬间摸向腰间的短刀,肌肉紧绷到了极点。
此时荣贵妃正卡在最关键的时候,孩子半个头在外面,只要我一动,她和孩子都得死。可如果不动,进来的人会立刻发现我们。
石门滑开一条缝,一道纤细的人影闪了进来。
不是皇帝,也不是禁军。
是一个穿着素白医女服的女人,手里端着一碗还在冒热气的黑汤。她看到这一幕,手里的碗猛地一抖,汤药泼了一地,那是令人作呕的腥味。
“别出声。”我压低声音,手中的短刀已经做出了投掷的姿势,“否则我让你脑袋搬家。”
那医女却没有尖叫。她死死盯着荣贵妃身下露出的那个婴儿头颅,眼里的惊恐瞬间变成了一种决绝的狂热。她快步冲过来,一把推开我的手:“让开!我是来送‘催命汤’的,既然没喝,那就得生下来!”
她是来杀荣贵妃的?不,不对。
医女迅速从怀里掏出一包银针,动作极快的封住了荣贵妃身上的几处大穴,低声道:“用力!孩子卡住了,不想死就听我的!”
“为什么要帮我们?”我握着刀,依然警惕。
“因为这个疯子杀了我的全家来炼丹!”医女咬牙切齿,眼眶通红,“他根本不是在求长生,他练的是邪术血婴丹!他需要至亲血脉的心头血做药引!这几年宫里的皇子,全都被他扔进了炼丹炉!”
我浑身一震,看向架子上那些琉璃罐。原来那不是废料,那是药渣。皇帝借种生子,不是为了继承大统,而是为了圈养“药材”。
“哇——”
一声响亮的啼哭骤然炸响。
医女眼疾手快,一把捂住婴儿的嘴,但那声音已经在密室里回荡了一瞬。
是个带把的。
这孩子浑身青紫,皱巴巴的,像只剥了皮的猫崽子,却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骨血。
就在这时,密室外传来了那个让我刻骨铭心的声音——那个威严、低沉,却透着一股阴邪气的男声。
“刚才是不是有动静?打开密室。”
是皇帝。
脚步声逼近门口,那种特有的龙靴踏地的沉重感,每一下都像是踩在我的心脏上。
医女脸色惨白,她迅速剪断脐带,胡乱用那件染血的龙袍把孩子一裹,塞进我怀里。
“这后面有个排污水的暗道,直通护城河。”她指着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井盖,眼神凄厉,“快走!带着这孽种走!让他长大后来杀了这个老畜生!”
“那你呢?”荣贵妃虚弱的伸出手。
“得有人挡着。”医女惨笑一声,抓起地上的手术刀划破手臂,尖叫着冲向密室大门:“有刺客!刺客往那边跑了!!”
“砰!”
密室大门洞开,我抱着孩子,拖着荣贵妃跳进那条漆黑腥臭的暗道。
就在井盖合上的最后一秒,我听见了一声利刃入肉的闷响,和医女戛然而止的惨叫。
07
我们在那条充满腐烂老鼠和淤泥的暗道里爬了整整一个时辰。
出来时,已经是皇城外的乱葬岗。暴雨还在下,冲刷着我们身上的污秽,却冲不掉那种深入骨髓的寒意。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活在噩梦里。
皇帝疯了。他发出的海捕文书,悬赏的是当夜出生的所有男婴,宁可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
除了朝廷的鹰犬,江湖上的赏金猎人像闻到血腥味的鬣狗一样蜂拥而至。
我仿佛又回到了十年前做杀手的日子,甚至比那时候更狠。
在湘西的密林里,我用藤蔓和尖竹做了“绊马刺”,把三个追踪的高手捅成了蜂窝;在破庙的废墟下,我埋了自制的土火药,把一队伪装成商贩的禁军炸上了天。
但我快撑不住了。
不是我,是荣贵妃。
那天在密室的生产太仓促,加上这一路的雨淋水泡,她产后大出血,高烧不退。
此刻,我们躲在一个废弃的炭窑里。她躺在干草上,脸色呈现出一种灰败的死气,身下的草甸已经被黑血浸透。那孩子因为没有奶水,饿得哭声都像小猫叫,只能吮吸我手指上沾着的露水。
“我不行了……”荣贵妃那双曾经顾盼生辉的眼睛,此刻已经浑浊不堪,她死死抓着我的衣袖,“别管我了……带着孩子……走……”
我摸了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如果不找郎中,不弄点止血的药,她活不过今晚。
可如果进镇子找郎中,我们的行踪就彻底暴露了。
身后,大内侍卫统领刘横——那个曾经和我并肩作战、如今却是皇帝头号走狗的男人,正带着最精锐的“黑骑”在十里外搜山。
救她等于送死。可不救,我就得眼睁睁看着我的女人死在面前。
我看着怀里那张皱巴巴的小脸,又看了看荣贵妃那张几乎没有人形的脸。
“等着。”
我把孩子塞进她怀里,从靴子里拔出那把已经卷刃的断刀,在石头上狠狠磨了两下,火星四溅。
“我去给你找药。阎王爷敢收你,我就去把地府拆了。”
08
白沙镇,济世堂。
我像是从地狱爬出来的恶鬼,浑身裹满泥浆,一脚踹碎了药铺的门板。
掌柜的还没来得及尖叫,我的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止血散,人参,还有干净的绷带。快!”
一包包药材被我塞进怀里。我不敢停留,扔下一锭带血的金子转身就跑。
然而,刚冲出巷口,我就停住了。
雨停了,月光惨白地照在青石板路上。巷子的尽头,刘横骑在高头大马上,手里提着一杆长枪,身后是几十名黑骑卫,个个手持强弩,封死了所有的退路。
而在刘横的马蹄下,跪着两个人。
那是昨天收留我们在柴房躲了一夜的哑巴老头和他那个只有七岁的小孙女。###修罗归来,再无软肋
小女孩被五花大绑,嘴里塞着布团,瞪大的眼睛里满是泪水,一颗颗往下掉。那是唯一给过我孩子一口米汤喝的人。
“修罗,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刘横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你还是那个臭脾气,为了个女人,连命都不要。”
“放了他们。”我握紧了刀柄,指节发白,“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道规矩。”刘横枪尖一挑,抵在小女孩的喉咙上,枪刃划破皮肤,渗出一线血珠,“把那对母子交出来,我给你留个全尸。否则……”
他手腕微微用力,小女孩呜咽着,拼命摇头。
我看到了那女孩眼中的求助,也想到了炭窑里奄奄一息的荣贵妃,还有那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投降,我们一家三口都得死。反抗,这对祖孙立刻没命。就算我杀了刘横逃走,只要她们活着,就一定会供出炭窑的方向。
人性?
这东西在皇权的碾压下,比纸还薄。
“刘横,”我突然笑了起来,笑声沙哑难听,“你错了。当年的修罗刀,没有软肋。”
话音未落,我动了。
我反手掷出药包,漫天的药粉瞬间炸开,遮蔽了所有人的视线。
同一时间,我手中的断刀化作一道寒光,扑向了另一侧。
“噗!噗!”
两声闷响。
我冲出迷雾时,地上多了两具尸体——那对哑巴祖孙。
我的刀划过小女孩的脖子时,她的眼睛还看着我,充满了不解。
但我不能停。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那个炭窑的位置。只有让刘横以为我毫无人性,他才会对我产生那一瞬间的迟疑。
“你……”刘横那张冷硬的脸上第一次变了颜色,“你真成魔了?”
“啊!”
我发出一声咆哮,趁着他们迟疑的瞬间,踩着小女孩尚未变冷的尸体腾空而起,断刀直取刘横的咽喉。
这一刻,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碎了。那个心软的焚尸匠死了。
回来的,是修罗。
09
北境的风卷着雪粒子,刮在脖子上生疼。
我们已经在雪原上逃了整整三天。荣贵妃趴在我背上,身体轻飘飘的,只有那忽冷忽热的体温,提醒我她还剩一口气。
前方就是雁门关。只要跨过去,就是北狄的地界,那时候天高皇帝远,我就能给这娘俩挣一条活路。
“到了……”我喘着粗气,嘴里喷出一团白雾,“再忍忍,过了这道关……”
咚——咚——咚!
就在我的靴子即将踏上关口吊桥的瞬间,三声沉闷的战鼓从城楼上炸响,震得雪层扑簌簌往下掉。
死寂的城墙上瞬间亮起无数火把,烧红了夜空。城头立着的,是一面巨大的、绣着五爪金龙的明黄旗帜,在风雪中猎猎作响。
“朕的好弟弟,你这脚程可是慢了点。”
城楼之上,一个身披金甲的男人负手而立。隔着百步远,我也能看清那张和我有着三分相似,却透着一股阴戾之气的脸。
皇帝。他竟然御驾亲征,堵在了这最后的生门上。
我浑身僵硬,怀里的婴儿似乎感应到了那股杀意,突然尖声哭了起来。
“把孩子交出来,朕给你留个全尸。”皇帝的声音被内力裹挟着,在山谷里轰然回荡。
“你是为了这个?”我解下背上的荣贵妃,让她靠坐在桥头的石狮子旁,拔出了那把早已卷刃的断刀,护在身前,“他是你的亲骨肉!虎毒尚且不食子,你为了练那劳什子邪术,连自己的种都要杀?”
“朕的种?”
皇帝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仰天狂笑,眼泪都笑了出来。他猛地收声,指着我,眼神怨毒:
“你也配提朕的种?你以为先帝为什么把你送出宫?为什么让你当个见不得光的影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因为你才是先帝遗落在民间的孽障!你是朕同父异母的野种弟弟!”皇帝吼道,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而这个孩子,是用你的血脉和荣贵妃的极阴之体,生出来的真正药引!只有用你们父子俩的心头血祭天,朕的血婴丹才能大成!”
原来如此。
借种,绝后,全都是局。
从十年前我被选为影子,到那晚的醉酒,再到如今的追杀,他要的不只是我的命,而是要榨干我每一滴血。
“动手!”皇帝失去了耐心,大手一挥,“要活的,别把血弄凉了!”
10
退无可退。
我们被逼进了一座废弃的烽火台。四面八方都是黑压压的禁军,围得水泄不通。
荣贵妃靠在墙角,嘴角的黑血怎么也擦不干净。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此刻已经开始涣散。
“别费劲了……”她按住我想要给她输气的手,惨然一笑,“我知道……我大限到了。”
“闭嘴。”我咬着牙,眼眶发酸,“老子把你带出来,就没想让你死。”
“听我说……”荣贵妃突然来了力气,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脸贴到我面前。血腥味里,还残留着一丝脂粉香。
“那晚……我没有被灌药。”
我愣住了。
她看着我,眼泪大颗大颗的砸在我手背上:“我在潜邸的时候就见过你练刀。那晚我知道是你……我是自愿的。”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几乎无法呼吸。
“这孩子……生来带毒……”她颤抖着从香囊里倒出一颗赤红丹药——她进宫前家里给的保命丹,仅此一颗,“只能救一个。”
说完,她直接掰开婴儿的小嘴,把那颗能救她自己命的药丸塞了进去。
“带着他……走……”
她的手抚上我的脸,指尖冰凉。那个“走”字刚落下,她的手便无力的垂了下去。
烽火台外,喊杀声震天。烽火台内,死一般的寂静。
我抱着孩子,看着那个到死都没能听我喊一声名字的女人。
一股空洞的感觉冲上我的头顶。人性被剥离后,只剩下冷静。
我撕下身上仅剩的一块干布,把孩子死死的绑在胸口,正对着我的心脏。
“儿子,别怕。”
我捡起地上的一块磨刀石,那是烽火台里唯一的硬物。
“滋啦——滋啦——”
我一下一下的磨着那把卷刃的断刀。每一声摩擦,都像是在给外面的十万大军敲响丧钟。
刀光映着雪光。
我不再是焚尸匠,也不再是修罗刀。
我是个死了女人的父亲。
11
轰!
腐朽的木门被我一脚踹碎。
风雪倒灌,吹得我乱发狂舞。我光着膀子,身上纵横交错的疤痕在火光下格外狰狞。
外面的禁军被这气势震得齐齐后退了一步。
“杀!”
没有废话。我直接扎进了黑压压的人潮里。
刀断了,我就用手撕;手断了,我就用牙咬。
我利用这雁门关狭窄的地形,专门往人堆里钻。每一次挥刀,必有一蓬血雾炸开。滚烫的鲜血喷在我脸上,瞬间被寒风冻成红色的冰渣。
“放箭!放箭!”有将领在后面嘶吼。
嗖嗖嗖——
漫天箭雨落下。我不躲不闪,硬生生的用后背接下了这一波箭。
噗!噗!噗!
七支羽箭钉在我的背上,痛觉早已麻木。我甚至借着这股冲力,往前又杀出十步,一刀削掉了那个发号施令将领的脑袋。
我的血顺着胸膛流下,浸透了包裹孩子的布条。
奇怪的是,孩子竟然不哭了。
他在尸山血海的战场上,睁着乌黑发亮的眼睛,静静的看着我。那眼神干净,没有一丝杂质。
那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
“吼——!”
我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咆哮,一脚踢翻了旁边的火油桶,火折子顺势扔下。
熊熊烈火在雪地里冲天而起,隔断了追兵的视线。我背着一身的箭,拖着那把已经砍得只剩半截的断刀,踩着尸体,一步步走向那面明黄色的龙旗。
皇帝坐在战马上,那张嚣张的脸变了颜色。他看着我这个浑身插满箭矢、浴血走来的身影,连马缰都握不住了。
“护驾!护驾!”
亲卫军蜂拥而上。
杀不完,根本杀不完。
我的体力飞速流逝,眼前开始发黑,耳边只剩下自己破败的喘息声。
就在我挥刀砍翻最后一个亲卫,踉跄着冲到皇帝面前时,我的膝盖一软,跪倒在地。
力竭了。
皇帝看出我已是强弩之末,脸上的神色转为狰狞。他拔出腰间尚方宝剑,剑锋一转,恶毒的刺向我胸口的孩子:“朕得不到的药引,那就毁了它!”
12
那一剑又快又狠。
我那不听使唤的手臂,在这一瞬爆发出惊人的速度,没有去挡剑,反而用那只露出白骨的左手,死死抓住了刺来的剑刃。
剑锋瞬间切断我的手掌,卡在骨缝里。
“啊——!”
剧痛让我清醒,我借着这一抓之力猛地前扑,一口咬住了皇帝的喉咙。
噗嗤!
腥热的动脉血灌进我嘴里。皇帝瞪大了眼睛,手中的剑哐当落地。他怎么也没想到,拥有武功和权力的自己,会死在这样一口撕咬之下。
与此同时,我右手早已准备好的最后一枚震天雷被我拉开了引信。
“一起下地狱吧。”
我含混不清的嘶吼着,抱着皇帝滚下了陡峭的悬崖。
轰隆——!
爆炸声引发了雪崩。
那一夜,半个雁门关被白雪和烈火吞没。大梁的皇帝,传说中的修罗刀,连同那个孩子,全都埋葬在了这片雪原之下。
……
七年后。
北狄边境,落雪镇。
镇东头有家不起眼的铁匠铺。铺子里的独臂铁匠是个哑巴,脸上满是烧伤的疤痕,看着吓人,但打铁手艺很好,只是从不打兵器,只打农具。
“爹!你看我削的刀!”
一个虎头虎脑的七岁男孩从外面跑进来,手里举着一把粗糙的木刀,舞得虎虎生风。
铁匠停下手里的大锤,用仅剩的手擦了擦汗,接过木刀看了一眼。他那张狰狞的脸上,罕见的露出了一丝淡笑。
他摸了摸孩子的头,指了指远处的雪山。
那是他们每年都要去祭拜的地方。
“张大娘问我,我娘埋在那,那我爹是谁啊?”小男孩眨巴着大眼睛问。
铁匠愣了一下。
他转过身,看向那座大山。山上终年积雪,埋葬了无数秘密。
他没有回答,只是重新举起沉重的铁锤,重重砸在烧红的铁块上。
“当!”
火星四溅。
这世上再无修罗刀,也无大内禁忌,只有一个想让儿子平安长大的父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