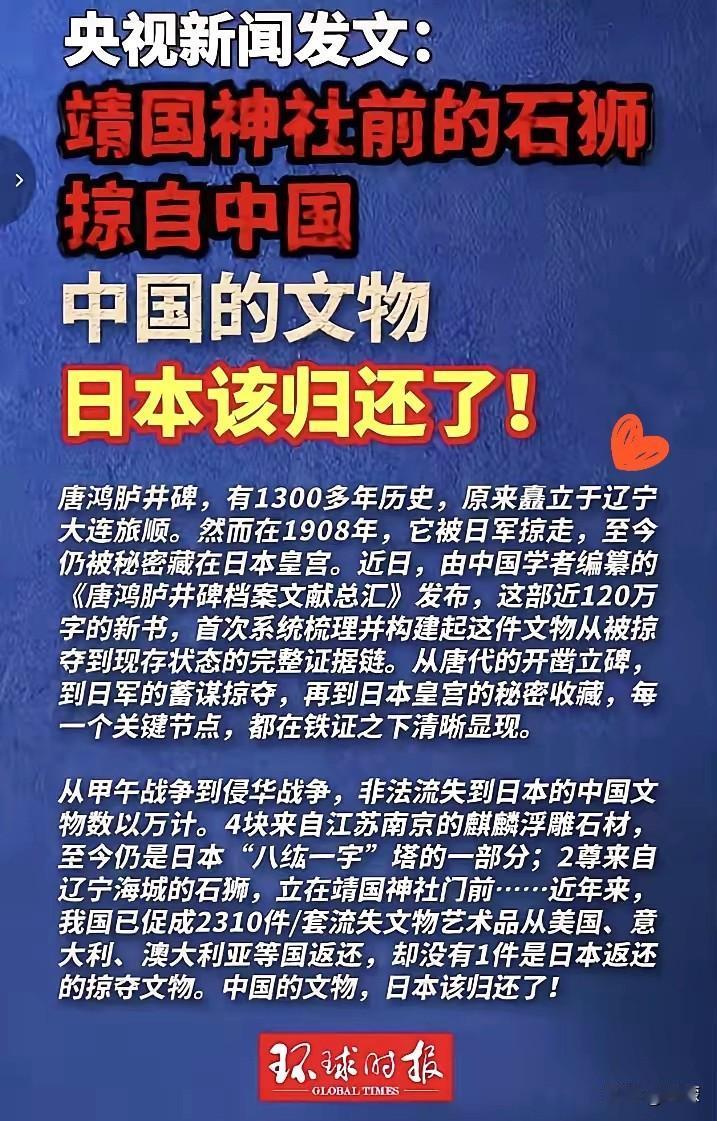关于我的名字
我家姓赵。我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三十一代孙,名叫元任。“元”是我的辈分,“任”是名字里头代表我个人的字儿。因为中国的姓比较少,两个字的名要是简化为一个字母,写成 Y. Chao,就会很容易重名,八亿中国人里头大概有七十万叫 Y. Chao 的。如果“元任”两个字分开来写,像西方人名那样写成两个名,重名的人会减少到二十六分之一,大概有两万七千人。所以在美国,中国人把两个字的名分开来写的情形很是普遍。人家叫我“元”而不是“元任”,就是这么来的,我太太在第三卷里头也叫我“元”。

一、东一片儿西一段儿
人人大概都有这种经验:回想到最早的时候儿的事情,常常儿会想出一个全景出来,好像一幅画儿或是一张照相似的,可是不是个活动电影。比方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四岁住在磁州的时候儿,有个用人抱着我在祖父的衙门的大门口儿,满街摆的都是卖瓷器的摊子,瓷猫、瓷狗、瓷枕头、瓷鼓——现在一闭眼睛——哪怕就不闭眼睛——磁州的那些瓷器好像就在眼前一样。可是这一景的以前是什么事情,后来又怎么样,就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
又有一幕,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儿,我们下半天常常儿有点心吃,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没人看着。赶我一走到那儿,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的吃起来了。我就说:“猫雌我的灭!”后来好像他们给我又盛了一碗面,可是我不大记得了。
还有一景,我每次碰到月亮好的时候儿就会回想到的。是在冀州,也是在我祖父的衙门里。我记得我跟我大姊、二姊、哥哥,我们四个人在左边儿一个跨院儿里赏月。我说“左边儿”,因为从住的地方儿望外走,那个院子是在左边儿。那么平常衙门的房子照规矩既然都是朝南的,左边儿那个跨院儿当然就是东跨院儿了。我还记得院子当间儿有两个大花台,每个花台当间儿有一棵树,是桂花儿是什么记不清了。我记得最真的就是那天晚上很冷,月亮格外的亮,好像人跟东西都不大有影子似的。照这样算起来那一定是冬天的事情了。可是除了我们四个人站得花台的南边儿赏月,什么事情也不记得了。
又有一回,是看吕爷种葫芦——吕爷是我们家里的一个男用人。那时候儿我们大概是住在保定。说起种葫芦来,当然总是好几个月,再不横是一夏天的事了。可是这一篱笆的葫芦,从栽子儿到长大,开花儿,结果,我就只记得两幕。一幕是地下一排小绿芽儿,吕爷在那儿给他洒水。再一幕就是满篱笆挂的都是葫芦了。当间儿开的是什么样子的花儿——照理应该是白花儿吧?可是一点儿也不记得了。所以这回事情,虽然占了有好些日子,可是我就光记得里头两景,所以还就是两张画儿似的。
后来我大了一点儿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就不全是一张一张的西洋景,就成了活动电影了。比方我五岁住保定的时候儿,有一个叫周妈的老妈子,他是看我的老妈子。有一天他在院子里在一个大木盆里洗衣裳。衣裳蘸了水,洗的时候儿一揉,不是常常儿会弄成鼓出来的气泡儿吗?我老喜欢看周妈弄。他要是不弄泡儿了,我就叫他弄,我说:“我要敌动达道!”意思是说:“我要一弄大泡儿!”其实我那时候儿已经会说话了,就是要成心装小,所以要假装儿着说不清楚话似的。那回我还记着周妈蹲得衣裳盆子的东边儿或是东南边儿,我站得盆子的北边儿看——因为北边都是平地,街道跟房子都是方方正正的,所以我们总记着东南西北是哪儿。这一幕固然已经是活动电影儿了,里头的事情都有点儿变动了,可是前后是跟什么别的事情接起来,就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还有一幕我记得很真的,是有一回动身搬家的前一晚上,好像是预备从祁州搬到保定。大家整天忙着齐行李,捆箱子,到了夜里睡觉的时候儿,除了铺盖没打以外,什么都归置好了,所以到处屋子里都是空空的,都不像个家里似的了。我虽然一小儿跟着家里差不多每一两年就搬一次家,可是看着家里这么变了样子,总觉着有点儿担心。我还记得我跟我妈睡在一间大屋子的东北角儿的大床上,我睡得外边儿,妈睡得里边儿,一盏油灯点着。平常睡觉谁先睡着谁后睡着轧根儿就不觉得。可是那天晚上啊,我一看见妈睡着了,我就大哭起来了。妈被我这么一闹醒了连忙问我说:“什么事?怎么啦?”我说:“妈先睡着了嘿!”这个解释现在想想——甭说现在,就是不久以后,也觉着很可笑,可是当时我觉着妈先睡着了就好像全家都走了,把我一人儿给遗了下来了似的,就觉着孤悢的不得了了似的。
最有意思的一幕回忆是在冀州看月蚀。这回事情是第一回我记得的有年月日的事情。我自然知道我生在天津的紫竹林,我是在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生的(就是西历1892年11月3日)。生的以前他们还预备了针,打算给我扎耳朵眼儿,因为算命的算好了是要生个女孩儿的。赶一下地,旁边儿的人就说:“哎呀,敢情还是个小子呐!”这大概是我生平听见的第一句话。
可是这些自然都是后来人家告送我的话,哪儿能算我真记得的事情呐?这回在冀州看月蚀啊,那是有真凭实据的日子了。我记得那时候儿我祖父做冀州直隶州的知州。我那时候儿照中国算法是七岁,那么应该是在1898左右。那回的全蚀是在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儿。这就有法子考了。按我的朋友黄授书先生的考据,那次月蚀一定是在阳历12月27日格林维基天文时23时38分,算起来就是在中国28日晚上七点钟左右,跟我记着的时候儿完全符合了。算日子么,该是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照那时候儿的规矩,凡是天狗要吃月亮或是要吃太阳了,大家就得拿着锅呀,桶子啊,乓呤乓啷的打,好把那天狗吓的把月亮要不太阳又吐出来了。当地方官的,像我祖父做知州的,又得穿起袍褂来一次一次的行礼,外头挂着许多旗子幔子咧什么的,像过年似的那么热闹。我不记得他们放鞭炮没有,可是记得他们吹号〔一〕打鼓。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从家里住的地方儿走到外头祖父坐堂的地方儿,我从右边儿出来往左看,就是往东南看,看见那月亮好像月牙儿似的,可是又不像平常的月牙儿。赶月牙儿越变越小,后来小到应该没了的时候儿,他并没有没,反倒变成了个红红的一个大圆的,看着都怪害怕的。那时候儿自然也没人给我讲什么折光作用把全地球四周的晚霞都射到月亮上,把整个儿月亮照红了。横是那时候儿就是有人讲给我听,我也听不懂的。可是那阵子我对天上的东西总是喜欢看,也喜欢跟人家问。这一次看月蚀的经验自然更是格外清楚。
〔一〕“吹号”就是吹一种长的铜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