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通,老人得知大女儿重病,多次去探望女儿,均被外孙拒绝,外孙说自己担心外婆悲伤过度,身体承受不住,另外他和三个姨妈矛盾很大,早已断绝来往。老人傻眼:自己的女儿自己还不能看了,哪有这样的道理?调解无果后,她一纸诉状,将外孙告上法庭,法院判了。 近九旬的邹婆婆,只想在有生之年再看一眼重病昏迷的女儿,谁知这个再朴素不过的愿望,却成了奢求。挡在她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外孙。 事情的起因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2023年4月,邹婆婆的大女儿吴女士因中风陷入深度昏迷,被送进康复中心接受护理。 得知消息后,年迈的邹婆婆心急如焚,在其他女儿的陪同下多次前往探望,却回回都被拒之门外。康复中心的解释很明确:吴女士的监护人是她的儿子程先生,没有他的同意,谁也不能探视。 于是,邹婆婆找到了外孙程先生。可程先生的态度异常坚决,他给出的理由听上去也颇为“周全”:一来,外婆年事已高,怕她看到母亲病重的样子受不住打击。 二来,他和几位姨妈也就是邹婆婆的其他女儿积怨已深,早已不相往来,他担心姨妈们会借探望之名,行干涉之事,激化矛盾。在他看来,外婆想来探望,背后少不了姨妈们的“怂恿”。 程先生的这份“孝心”和“戒心”,却成了隔绝祖孙三代亲情的铜墙铁壁。他干脆利落地拒绝了除自己以外所有亲属的探望请求。为了见上女儿一面,邹婆婆想尽了办法,反复沟通无果,报警求助无用,社区调解也陷入僵局。 日复一日的思念与隔绝,让这位老母亲备受煎熬。到了2024年12月,在用尽所有温和方式后,她一纸诉状将亲外孙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决她每月能探望女儿一次。 这起案件的症结在于,法律上存在一个模糊地带。中国的《民法典》明确规定了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探望权,但对父母探望成年子女,尤其是像吴女士这样无法自主表达意愿的成年子女,却没有清晰条文。 程先生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在法庭上辩称,母亲是成年人,外婆在法律上并无探望权。他还强调,母亲身体极其虚弱,任何微小的感染都可能致命,不适合频繁探望。 邹婆婆的诉求简单而纯粹。她告诉法官,自己头脑清醒,去看女儿是她自己的决定,与旁人无关。她也承诺,会严格遵守康复中心的一切规定,绝不给女儿的治疗添乱。她要的,不过是一位母亲看望病倒孩子的权利,这种源自天性的情感,不该被家庭矛盾所绑架。 社会舆论也因此事分成了两派。有人认为程先生做得太过火,与姨妈有矛盾,可以只拒绝姨妈,但不该把外婆也拒之门外。也有人觉得程先生作为监护人,他的担忧不无道理,既要防着老人身体出意外,又要防着亲戚闹事,索性一刀切,也是无奈之举。 法官认为,法律条文虽未直接规定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探望权,但《民法典》的总则精神是敬老爱幼、家庭和睦。 法律规定了父母对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仍有抚养义务,当子女因重病陷入这种状态时,探望权作为亲子关系最自然的体现,理应受到保护。这既不违法,也完全符合公序良俗。 程先生的担忧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他的做法过于极端,完全忽视了外婆作为母亲最基本的情感需求。以“为你好”为名的保护,若剥夺了至亲间最温暖的慰藉,便失去了意义。 法院判决,邹婆婆每月可在第二周的周日下午2点到5点探望女儿一次,程先生必须予以协助。判决同时明确,邹婆婆探望时须遵守院方规定,做好防护。 考虑到老人高龄,法院还贴心建议,可由其他女儿接送,并佩戴电话手表以防万一。程先生不服上诉,但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这场官司,不仅让一位母亲重新获得了看望女儿的权利,更在司法实践中,为“探望权”这一概念注入了更富人情味的解释,它提醒我们,家庭关系有时会复杂到需要法律的介入,而法律最终要守护的,恰恰是那些最简单的人性与亲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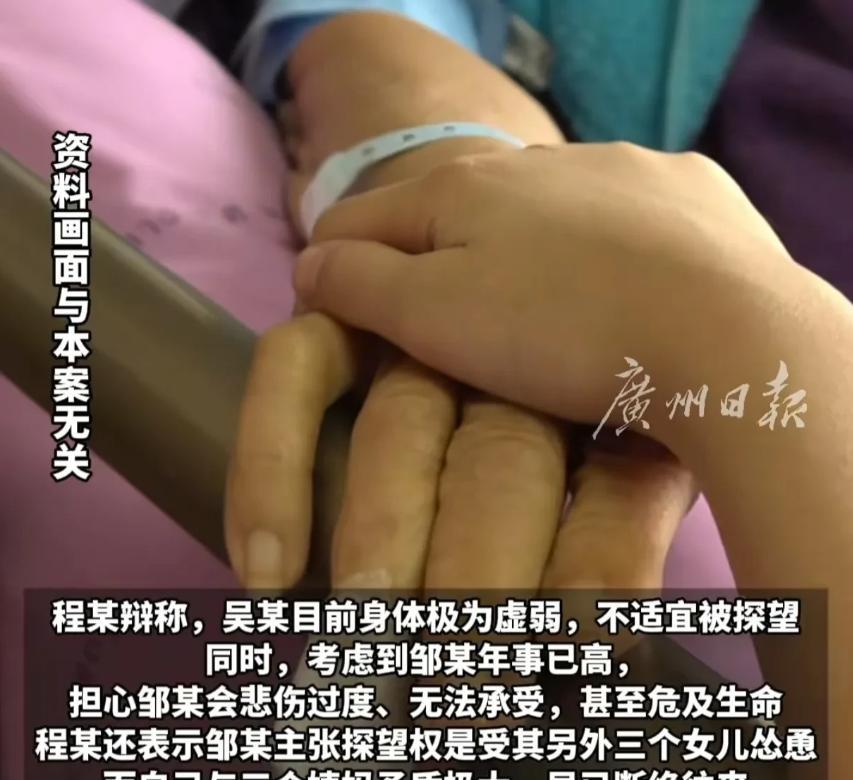

黄妞妞
难道怕90+的外婆继承财产…
东哥在三峡 回复 07-01 16:05
这个最可能!!!
御韵琴香
程先生有权利拒绝姨妈探视母亲吗?亲姐妹不能看?
风是自由的 回复 07-01 14:14
他有这个考虑不是没原因的,我爸亲弟就是白眼狼一个,骂他畜生都不过分。没准他姨妈就是这种人。
拣尽寒枝
母亲没有权利看望生病的女儿?奇葩。父母和儿女都是直系亲属
潮长安
真相难说,正常来说孩子敬爱父母的力度是比不上父母疼爱孩子的
鉴山沮水
混帐孙子❗
dahai9967
现代社会情商智商只会越越低,高不起来了!!!
红色感叹号
视频探视吧
用户10xxx05
这儿子一点也不孝顺。母亲想女儿,女儿也会想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