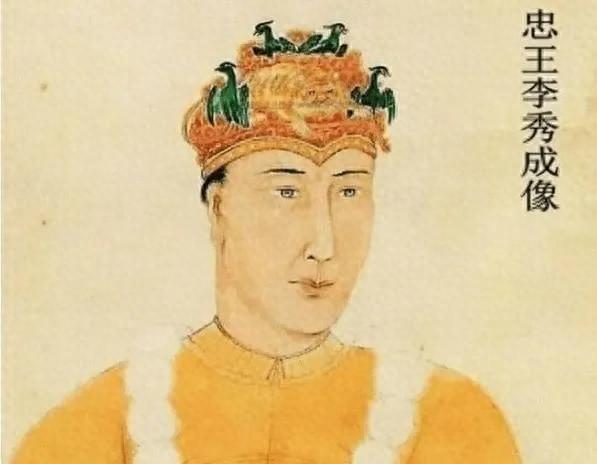1963年,溥仪在北京街道闲逛,看到一烧饼摊,于是便买了一个,没想到刚吃了一口,便咬牙切齿的说,那群死太监竟然骗了我40多年。 1963年的北京,夏天格外热,街道上人来人往,阳光晒得柏油路面都有些发软,西单街头,一家烧饼摊前,炭火正旺,烤炉里的烧饼泛着金黄的光,芝麻在高温下发出浓郁香气,空气中混着热浪与麦香,令人忍不住驻足。 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摊前,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褂,肩膀略微前倾,神情安静,他的手里拿着一个刚刚出炉的烧饼,面前排着几个人,摊主正忙着翻动烧饼和收钱,这人站在那里,并无特别之处,若不是细看,很难把他与“末代皇帝”这四个字联系起来,他叫爱新觉罗·溥仪,曾经的宣统皇帝,如今是北京植物园的园艺工人。 他用两根手指夹着烧饼,小心地换了几次角度,才找到了不烫的地方,咬下去的那一刻,烧饼外皮的酥脆和内里的柔软同时在口中展开,芝麻的香味瞬间涌上来,他的动作忽然停住了,眼神也凝固了几秒,那个味道,与他几十年前尝到的,截然不同。 几十年前,在紫禁城里,他也曾经听说过烧饼的名字,那时他年纪还小,听宫女们在一旁低声议论,说宫外的烧饼香得很,吃一口能让人整天嘴里都是香的,他心里起了好奇,想尝一尝,但出宫是不可能的,他只能让太监去买。 那个烧饼最终出现在他面前时,已经冷得像块砖头,咬一口下去,硬得硌牙,味道寡淡,根本没有宫女说的那种香气,他当时皱了眉,但太监却说这就是老百姓吃的东西,粗俗而难以下咽,他信了,从那以后,对烧饼的印象就停留在那里——冷、硬、难吃。 这一次站在街头,吃着刚出炉的烧饼,他忽然意识到,从前那些味道,根本不是真的,他被欺骗了,而且是被身边最亲近的人骗了几十年,他曾是皇帝,却连一口真正的烧饼都没能吃到。 他记得小时候在紫禁城里,生活看似富贵,其实处处受限,每天的膳食由御膳房照料,按理说该精致讲究,但他吃到嘴里的,常常是前一天剩下的饭菜,热一下就端上桌,御膳房的人早已没有心思精心烹饪,太监也只是敷衍了事,没人关心他的口味、喜好,更不会在意他想不想吃。 他坐在高高的龙椅上,脚够不着地,身边是一群鞠躬哈腰的人,他是皇帝,但又像是个被摆在台面上的瓷人,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他完全不知道,他唯一的窗口,就是那些刻意过滤后的话语,以及偶尔从宫外带进来的物品,他以为自己拥有一切,其实连最基本的真实都不曾拥有过。 之后的日子里,他的人生经历了剧烈的转折,从皇宫被逐,到天津做寓公,再到长春当“皇帝”,每一步看似权势在握,实则身不由己,他的身份只是个摆设,真正掌控他命运的,是那些在他背后操纵一切的人。 1945年日本投降,他被苏联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关押,在那里,他第一次脱离了皇帝的身份,开始面对自己的人生,他不再是“万岁爷”,只是一个被看管的战俘,1950年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他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 那是一段彻底颠覆他认知的时期,他开始学习读书、学习劳动,第一次亲自洗衣做饭,种菜扫地,他不再有人伺候,也不再有特权,只有一群和他一样等待改造的犯人,没有人对他卑躬屈膝,也没有人欺骗他,他开始明白,自己过去所处的位置,并不代表真实,他的世界太小,太封闭,太虚假。 1959年,他获得特赦,被正式恢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工作,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他学习修剪枝叶,学习用铲子挖土,学习点票、坐车、买菜,他住在胡同里,租了一间小房子,屋子不大,却比紫禁城里自由得多。 他结了婚,妻子是协和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生活平静而普通,他学会了生活中的各种琐事,比如怎么辨别新鲜蔬菜,怎么买便宜的日用品,他不再需要别人告诉他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也不再依赖别人的嘴来认知世界。 他开始留意街头的气息,观察人来人往,他喜欢在下班后绕道回家,看看市场上卖的东西,听听摊贩的吆喝,他第一次从内心感受到自己是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而不是被供奉在高台上的象征物。 那天吃到热烧饼的瞬间,所有的记忆一下子翻涌而来,他忽然明白,几十年来自己对食物的误解,其实就是对整个世界误解的缩影,他不恼了,只是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释然,真实的生活原来就在眼前,只是过去的他看不见、摸不到。 他开始写日记,用平实的语言记录每天的生活,日记里没有帝王的语气,只有一个普通人在花丛间劳作、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在家中与妻子分担家务的琐碎,他写得认真,字迹稳重,笔下的每一笔都像在与过去的一刀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