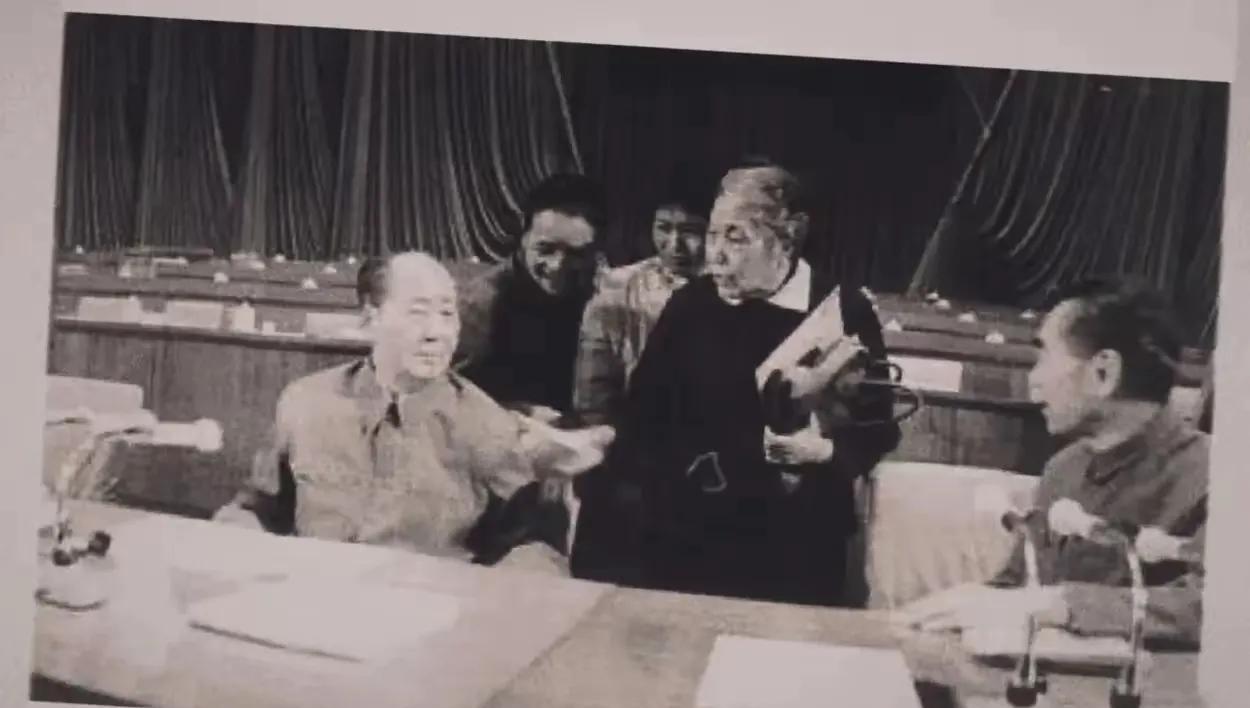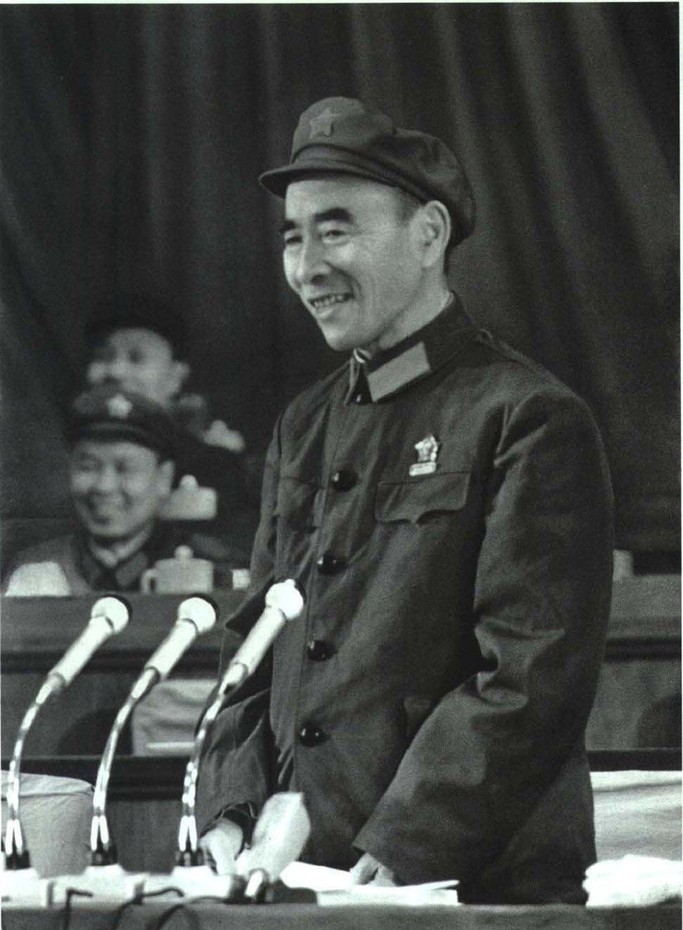1950年,毛岸英看望外婆向振熙,问她有什么要求,向振熙却说“我只要10万元。”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那年的长沙,空气中还残留着战火硝烟散尽后的尘土味,毛岸英拎着精心准备的贺礼走进外婆向振熙的老宅院时,院角的桂花树正飘着细碎的花瓣。
人参、鹿茸、崭新的衣料,这些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堪称奢侈的寿礼,却被老人轻轻推回了桌角。
老人布满皱纹的手在樟木箱里摸索许久,掏出的不是给外孙的压岁钱,而是一张边缘已经起毛的宣纸。
毛岸英接过来,毛笔字迹在三十年的时光里褪成了浅褐色,但"毛泽东"三个字依然力透纸背。
1920年的冬天,那个即将奔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青年,在岳母家灶台边写下的这张百元借据,像块烧红的炭烫得他手指发颤。
这笔旧币折算成新币正好十万元,在1950年相当于普通工人二十年的工资。
向振熙老人不是真要讨债,她颤抖的手指抚过借据上早已干涸的墨迹:"当年你父亲说,这钱要拿去救更多人的命。"
窗外传来街坊们庆祝土改分到田地的锣鼓声,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现在新政府成立了,我就是想看看,共产党人说的话还算不算数。"
毛岸英连夜给北京写信,中南海的灯光下,毛泽东盯着儿子寄来的泛黄纸片,记忆突然回到三十年前那个雪夜。
当时他变卖所有家当筹备革命经费,岳母偷偷塞给他的这笔钱,后来变成安源煤矿工人夜校的课本,变成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粉笔。
秘书拿着财政部的批件进来时,发现主席正用铅笔在日历上计算,按照解放区银行规定的革命债务年息,连本带利该还多少。
十天后,长沙人民银行来了三位穿军装的同志,他们没带成捆的钞票,而是抬着个沉甸甸的木箱。
打开是二十包用红纸封好的小米,每包五斤,这是根据地时期就沿用的折算方式,一斤小米抵一元钱。
向振熙老人抓起金黄的谷粒,泪水突然滚落在新中国的粮袋上,她执意只留一包,剩下的要干部们送去孤儿院,就像当年女婿揣着那笔钱走进安源煤矿的雨夜里。
这张借据后来被收入中央档案馆,和红军打给老乡的欠条、八路军留下的粮票收据放在同一个樟木柜里。
它们沉默地讲述着革命年代最朴素的契约精神:当年在油灯下写借据的青年,三十年后用国家主席的身份兑现承诺;那个在军阀混战时冒险资助革命的老人,最终在新中国的粮仓前笑着抹泪。
历史有时候就藏在这样的细节里,当毛岸英蹲在外婆膝前解释"现在全中国的粮食都是人民的"时,当老人把小米分给街坊说是"还利息"时,那张泛黄的借据突然有了温度。
它不再是博物馆玻璃柜里的文物,而成了连接两个时代的信物,关于承诺,关于信任,关于共产党人无论走多远都记得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