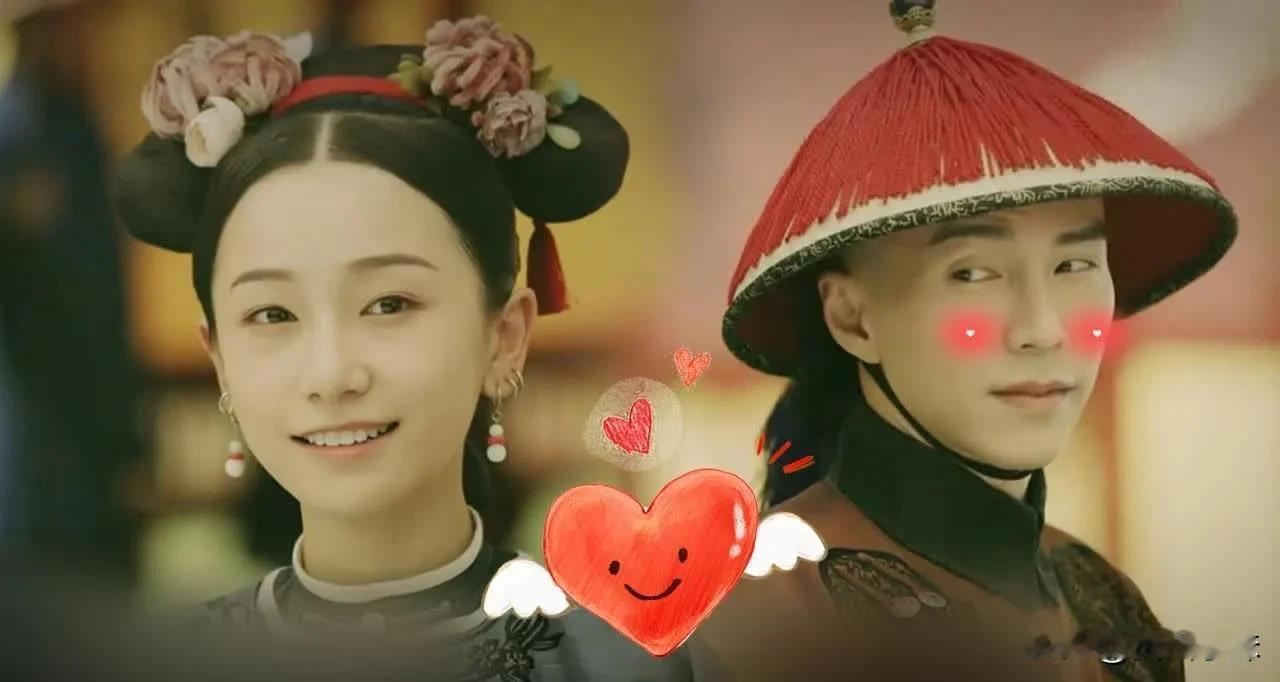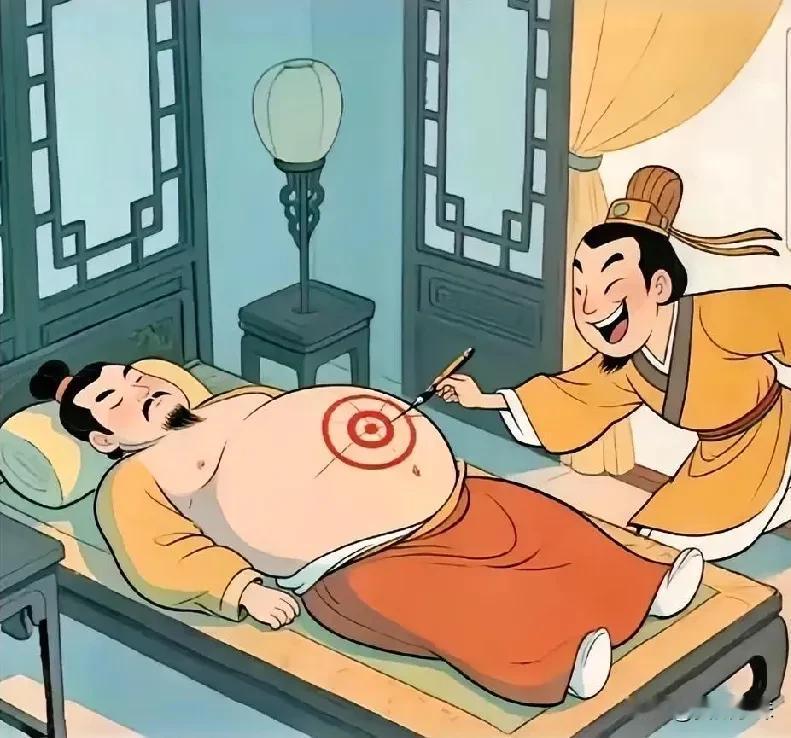1665年,康熙娶了年仅12岁的赫舍里氏。不料,洞房时赫舍里氏竟自己扯下了红盖头。康熙看着眼前的貌美女子,瞬间呆愣在原地。
正月初七的北京城飘着鹅毛大雪,紫禁城里的金銮殿上跪满了文武百官。
八岁的玄烨裹着明黄色龙袍坐在冰凉的龙椅上,两只小脚还够不着地面。
他还不明白"皇帝"这两个字的分量,只是觉得身上这件绣着金龙的袍子比平时穿的衣裳沉得多。
坐在帘子后面的孝庄太后看着孙子稚嫩的脸庞,手里的佛珠转得越来越快——顺治皇帝走得突然,留给这孩子的可是个烫手山芋。
四位辅政大臣里,镶黄旗出身的鳌拜嗓门最大,上朝时他总是把奏折摔得啪啪响,吓得小皇帝直往龙椅里缩。
孝庄太后夜里睡不着觉,数着更漏盘算:索尼是四朝元老,可年岁大了不爱管闲事,遏必隆是个墙头草,苏克萨哈倒是忠心,可惜势单力薄。
眼看着鳌拜把镶黄旗的兵马越调越多,老太太终于咬着牙下了决心。
那年春天柳树刚抽芽,十二岁的赫舍里氏正在家里绣花,忽然听见前院传来圣旨到了的吆喝声。
小姑娘跪在青砖地上,听着太监尖细的嗓音念着"册封皇后"的字句,手里的帕子绞成了麻花。
她祖父索尼在书房里踱着步子,老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这步棋总算没走错。
大婚当天,坤宁宫里红烛高照,康熙挑开珍珠门帘时,手指头都在打颤。
他听说过这位皇后是索尼家的姑娘,可鳌拜总在他耳朵边上嘀咕"满洲老姓家的丫头粗手大脚"。
龙凤喜烛哔啵爆了个灯花,新娘子突然自己掀了盖头,露出张白净的鹅蛋脸,水汪汪的眼睛像盛着星星。
小皇帝手里的金秤杆"当啷"掉在地上,外头守夜的太监差点冲进来。
要说这赫舍里家的姑娘确实不简单,进宫没半年就把各宫嬷嬷治得服服帖帖。
康熙下了朝总爱往坤宁宫跑,看着皇后带着宫女们在院子里踢毽子,绣着金线的裙摆翻飞得像蝴蝶翅膀。
有回鳌拜在乾清宫等了两个时辰,最后发现皇上蹲在御花园给皇后编花环,气得老头子的胡子直翘。
转眼到了康熙八年,太和殿前的日晷影子转了一圈又一圈。
这天早朝时,二十几个镶黄旗的侍卫突然把住了殿门,鳌拜刚要发火,就看见索尼颤巍巍地捧着先帝遗诏站出来。
少年天子从龙椅上站起来,腰间的玉佩撞得叮当响:"鳌少保,你是要朕给你挪地方吗?"
后来刑部的人说,那天从鳌拜府里抄出来的黄马褂,足够装备一支亲兵队。
坤宁宫的石榴树红了三次,赫舍里氏怀上了头胎,那段时间康熙批折子都要挨着皇后坐,听见胎动就傻笑。
可惜小阿哥没熬过百日就得了急病,赫舍里氏抱着绣金线的襁褓哭晕过去三次。
康熙把太医院的脉案翻了个遍,最后把方子摔在跪着的太医头上:"朕要你们何用!"
等到再次有喜讯传来,已经是康熙十三年春天,接生的嬷嬷们在产房忙活了整整一天一夜,孩子的啼哭声伴着更鼓声传出来时,康熙手里的茶杯早就凉透了。
赫舍里氏脸色白得像宣纸,手指头攥着明黄锦被直发抖:"保...保孩子..."
这话成了皇后最后的口谕,刚出生的胤礽在乳母怀里哇哇大哭,他永远都不会知道,母亲临终前盯着床帐上绣的龙凤,嘴角还带着笑。
乾清宫的铜鹤香炉从此再没断过檀香,年轻的皇帝把自己埋进成堆的奏折里,偶尔抬头看见墙上挂的《耕织图》,恍惚间还能听见银铃似的笑声。
有次南书房当值的小太监看见,皇上对着案头的水晶镇纸发了半天呆——那是皇后生前用来压绣样的。
后来内务府的人说,坤宁宫里的摆设再没动过地方,连皇后没绣完的荷包都原样摆在绣架上。
索尼家的老宅子这些年门庭若市,可赫舍里氏的父亲噶布喇再没进过宫。
听说他每次喝醉了就抱着孙子的长命锁哭,嘴里念叨着"要是当年没接那道圣旨"。
这话传到康熙耳朵里,皇上只是摆摆手,转身去了奉先殿。供桌上的牌位擦得锃亮,烛光照着"孝诚仁皇后"几个金字,晃得人眼睛发酸。
日子像护城河的水一样流着,紫禁城的琉璃瓦上落了又化二十场雪。
平三藩、收台湾、打噶尔丹,史书上记满了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
只有苏麻喇姑知道,每年腊月二十九夜里,皇上总要独自在坤宁宫前的汉白玉台阶上站会儿。
老嬷嬷抱着手炉缩在廊柱后头,听见风声里夹着声叹息,轻得像片雪花落在梅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