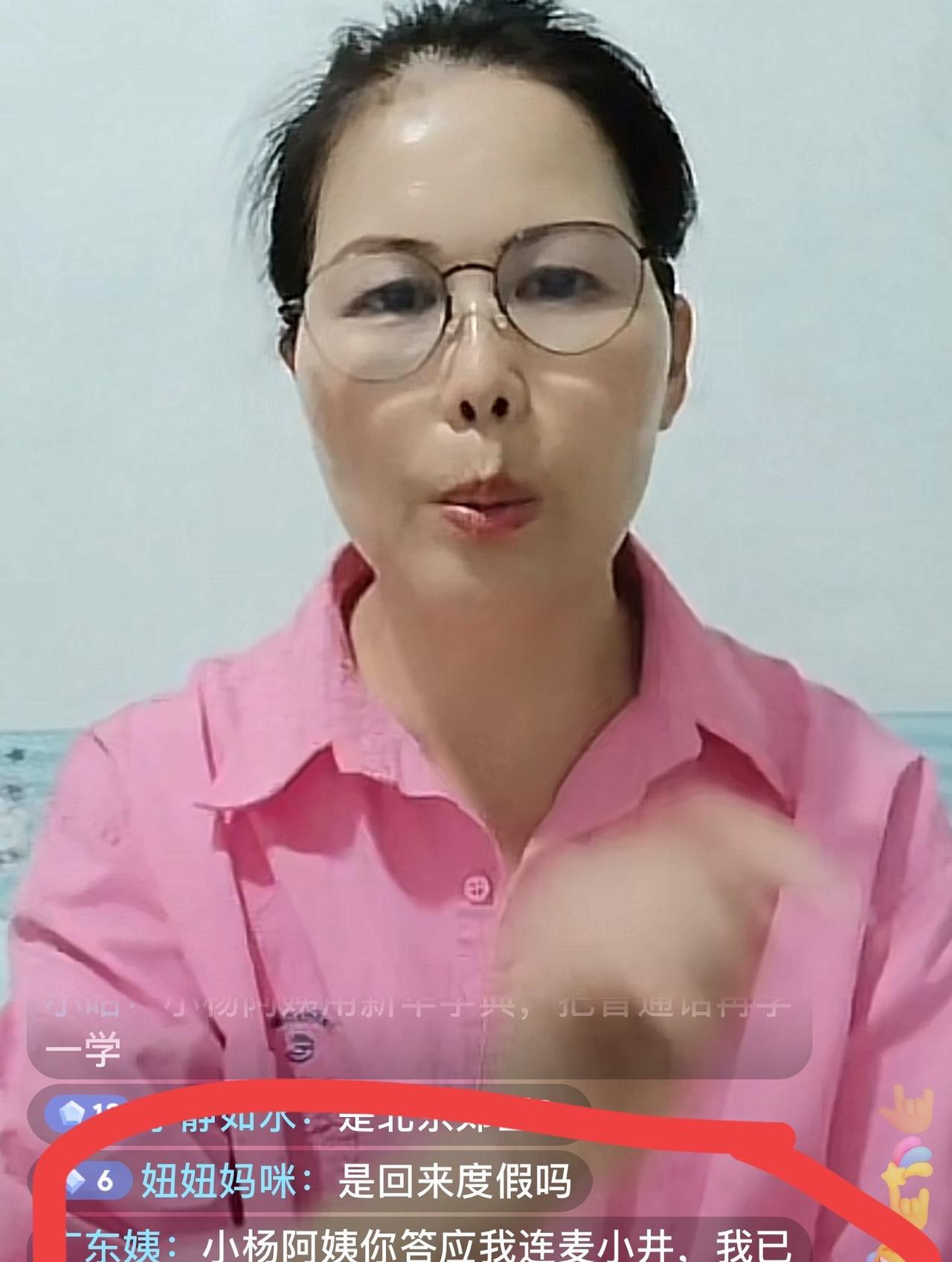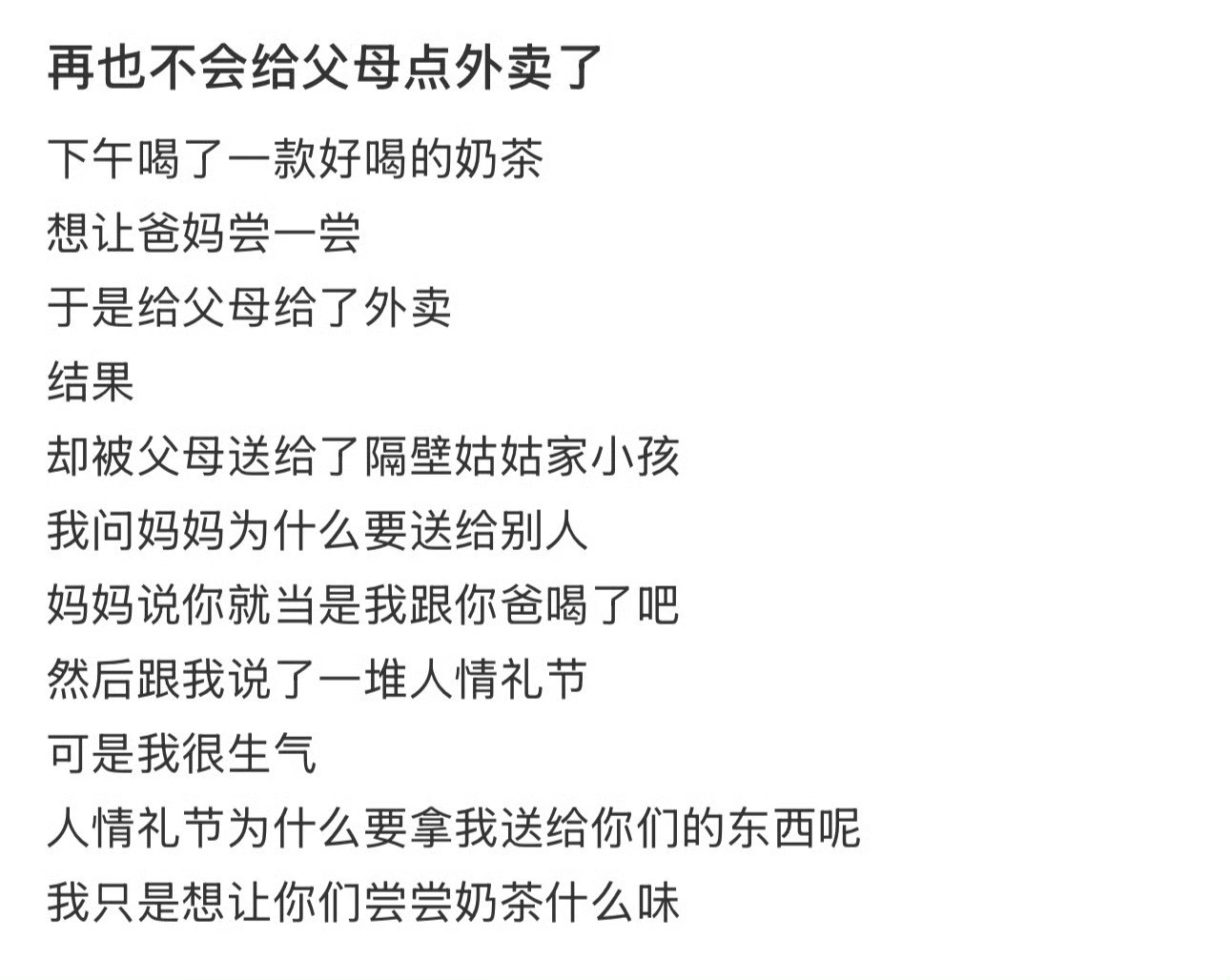1996年夏天,华盛顿一间写满公式的办公室里,记者突然发问:“彭教授,多少人盼您归来,您还回重庆吗?”话音刚落,空气几乎停滞。 彭云手里转着的钢笔突然停了,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大得吓人。 他眼前晃过重庆歌乐山那座总被游客围住的烈士墓——小时候老师带他去扫墓,同学偷偷议论“江姐儿子该当大英雄”,他攥着白菊的手心全是汗。 “母亲的遗愿,我只完成一半。” 这话他在北京说过,在美国说过,说一次心口就紧一次。江姐托孤信里“踏着父母足迹”的殷红字迹,像烙铁烫在纸上,也烫在他背上。可实验室里冰冷的计算机阵列亮着绿光,比渣滓洞竹签蘸棉灰写的遗书更让他看得清方向——每秒百万次的计算能力,国内研究所保险丝三天两头烧糊的电路板,差距大得让人喘不过气。 不是没试过回来! 八十年代在北京搞研究,办公室电扇吱呀乱响,夏天冰镇酸梅汤还没喝就化了。他看着窗外灰扑扑的筒子楼,想起养母谭正伦当年在煤油灯下给他补书包,针脚密得能绣花。可科研这活儿,光有绣花的耐心不够,得通电啊!美国出版社看中他论文那天,桌上躺着国内催他填的行政表格,厚得能当砖头。 有人嚼舌根说“江姐儿子在美国享福”,他听见当没听见。 倒是在马里兰大学的课堂上,他把密码学讲义翻到“红岩精神”那页特别标注:“我母亲用生命守护的秘密,比你们破译的算法珍贵千万倍”。127个中国留学生坐得笔直,后来全回国了——这算不算另一种“建设新中国”? 儿子彭壮壮的选择比他更狠! 普林斯顿博士毕业,微软高管当得好好的,突然打包回国。临行前夜,彭云偷偷往儿子行李箱塞了包重庆带来的土,泥巴里还混着歌乐山的碎石子。去年清明视频,彭壮壮站在江姐雕像前举着白菊喊:“爸,我给奶奶说了,芯片研发快出成果啦!” 屏幕这头,老头儿眼镜片上全是水汽。 烈士光环太重了,重得能把人压进土里。 江姐要的从来不是复制另一个自己,她遗书里写“粗服淡饭足矣”,盼的是儿子活得清白踏实。彭云这辈子没入美国籍,中国护照用到泛黄发旧。有次华人聚会举杯祝酒“为自由干杯”,他端着橙汁轻声说:“我母亲为自由死了,我替她好好活。” 重庆咏梧社区柑橘园今年大丰收,漫山金黄压弯枝头。 当年带头开荒的村支书卓琼,办公室里摆着彭咏梧小学的毕业照。她不知道,几千公里外的马里兰,有个白发教授总爱盯着橘子出神——养母谭正伦在他去留学前,颤巍巍往行囊塞了五斤广柑:“云娃,甜得很,莫忘了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