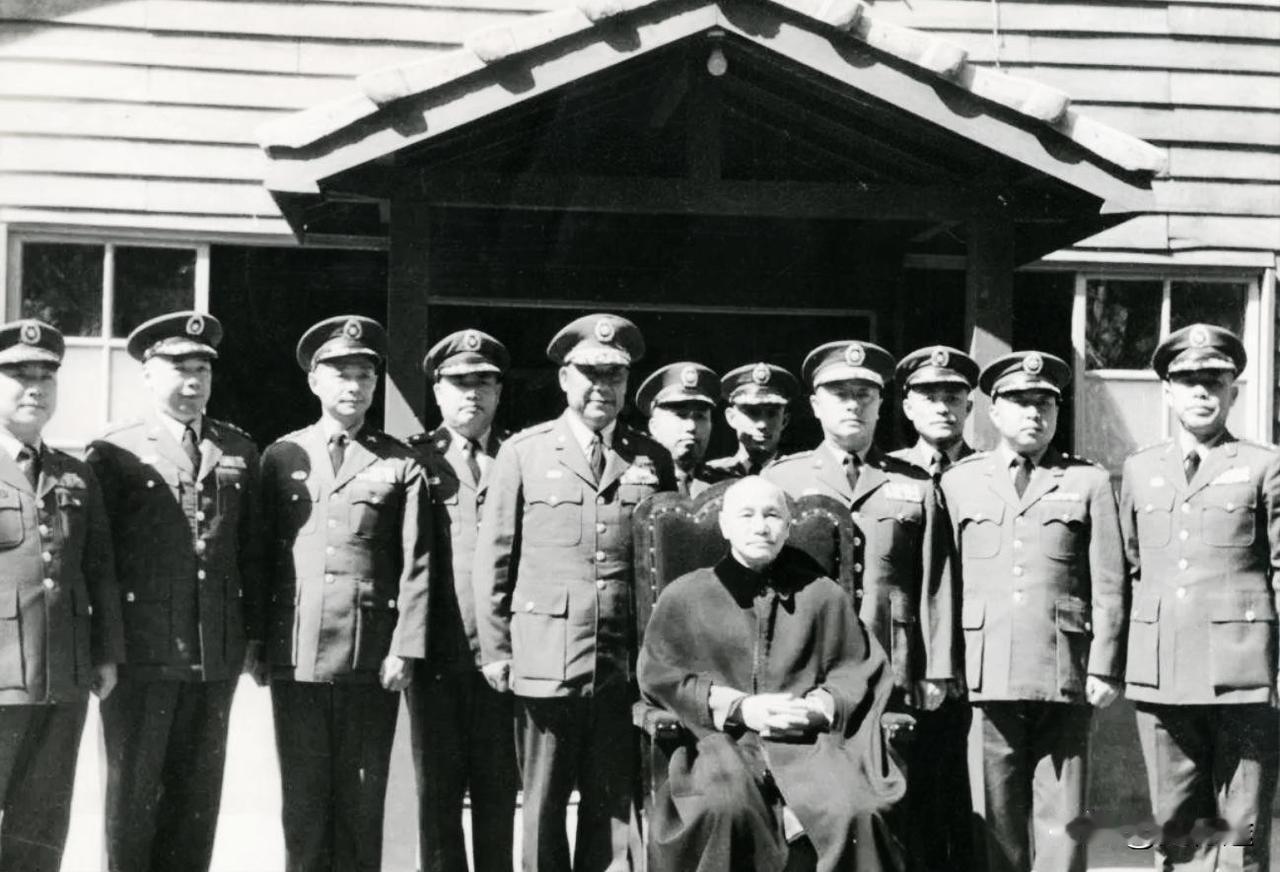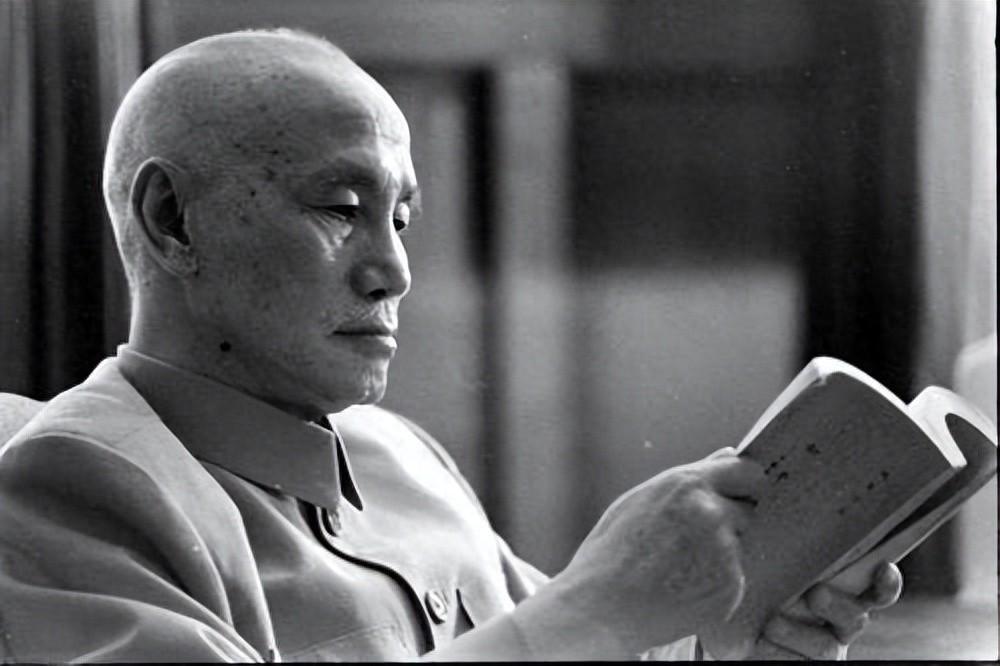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逼迫,交出兵权后考察散心,蒋介石也够意思,给了3万大洋路费,不想,王家烈前脚上飞机,后脚,特务就把他的贵州老窝给“端了”! 那年春天,贵阳的雨下得没完。 王家烈坐在窗边,不看雨,也不看报纸,只搓着一只旧烟斗。他已经搓了一下午了,烟斗没点上,烟草是潮的。他其实也不抽烟,只是拿着那玩意儿出神。 屋外是他亲自修的青石台阶,地滑,泥腥味浓。几个警卫悄悄挪进屋子,谁也不敢先开口。 他听说,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带着薛岳和一批新面孔。 薛岳他打过照面,不熟,眼神凶,讲话不留口德。他知道这趟来不是为了什么“督战红军”,督战是假,清算是真。 中央早就憋不住了,贵州这口锅,他们想端。 王家烈心里一清二楚,外头人叫他“贵州王”,叫得越响,南京那边就越想拔他的钉。 可话又说回来,他怎么来的?打出来的。 老黔军那时候穷得连棉衣都没有,一碗米饭掺着糠下肚,背着破枪守山头。 他是从桐梓一路打上来的,一路背人情,一路踩骨头。他不读书,不会讲什么“新政”、“整编”、“训政体制”,他只知道,贵阳的椅子是他坐上去的,凭的不是文告,是血。 现在要他下来,也得给他一个说法。 可蒋介石没有要给他说法的意思。那天谈话,地点选在贵阳行营,屋里点着煤油灯,一股生铁味,热得人发困。 蒋介石戴着白手套,手不多动,眼神却很忙。 他看着王家烈,说了句:“主席和军长,只能留一个。”语气轻得像说“饭里是放盐还是酱油”。 王家烈没答,他知道这句话背后是刀。带来的人已经进城,文告也准备好了,只等他开口投降。出去后他摔了茶杯,瓷碎在地上,半晌没人敢动。 他骂了一句脏话,说是“狗日的”,骂得不响,却结实。 第二天他答复了,留军职,不当省主席。那是他最后的执念,枪还在手,心还不冷。 过了没几天,军饷断了。不是晚,是直接停。 他派人去催,南京那边回话,说“账目混乱,待核实”,一句话,堵得死死的。 兵营里炸了锅,士兵拿着空饭碗敲锅,骂娘的、砸碗的、跑的都有。他清楚,枪在手也没用,枪杆子要吃饭。有人劝他回头,他不答。 他只是坐在老营部楼梯口,听着外头下雨。那雨下了一个星期,地上积着水,湿得能养青蛙。 他撑了不到两个月。 电报发出去那天,他穿了一身整军礼服,胸前的旧勋章擦得锃亮。 他站得笔直,像是还要打一仗,但没人给他仗打。他在贵阳机场上了飞机,身边是张学良,一起飞往武汉,再转南京。 飞机升空时,贵阳街头下起了小雨,城西的望城坡还飘着炊烟。 特务进城的时间点刚刚好,他人刚走,他们就封了旧军部,搬出一箱箱资料,拉走了几个人。 有老兵不愿走,被一脚踹倒在台阶上,鼻血滴在青石上,被雨水冲成一摊红泥。 三万大洋的“路费”,传得沸沸扬扬。他身边的人有人拿到了,有人没拿到。钱像烟一样散得快,几个月就花光了。有人说那是“封口费”,也有人说是“送客钱”,说什么的都有。他自己没回应。后来有人问他,他只说了一句:“是银子,不是脸。”说完低头喝茶,那茶泡了半天,早就凉透。 南京给他安了个“军事参议中将”的名号,挂了个名。 他住在中山陵附近的一处旧宅,每天早上出去散步,戴草帽,穿夹袄,身边跟一个年轻人提茶壶。路上碰见老军人,还有人跟他敬礼,他回得慢,但还是会点头。那几年里他几乎不说话,不进议事厅,也不写东西。他像是被挂起来了,像古庙里那口年久的钟,不敲也不响。 抗战开始,他被提了一次,任二十军团副军团长。 但没兵,没指挥权,只是挂名。他自己知道那是场戏,唱得不热闹,但不能下台。他接了,没推。再后来,战乱四起,他也不再出现于公众场合。 那时候,他的名字在军报上出现得越来越小,最后干脆不见了。 解放前夕,南京一片慌乱。 有人来劝他走,说船票和台湾那边的安排都办好了。 他坐在屋里看一本旧书,是本关于贵州地理的老书,封面已破。他不答,过了很久才摇头,说:“我走了,我妈的坟就没人烧了。”那天夜里,他点了一炷香,坐了一宿。 新政权建立后,他被安排了个职务,政协副主席,贵州省的。他回了贵阳,回得悄无声息,没人迎,也没人问。 他住在省政府后面的一排旧平房,门前有棵老槐树,风吹起来树叶响。 他常常一个人写字,写贵州的历史,说是要“留点正经的东西”。 他不讲旧事,不骂旧主,也不念旧仇。有人去访,他也不拒,坐下来泡一壶茶,只讲山里的气候、风土、人情,说得缓慢,说得仔细。那茶不热,话却温。 他晚年写了十几本小册子,都是关于黔地风俗的。 1966年夏,他病了。 高烧不退,眼睛睁不开。住院那几天,病床边只有一把破蒲扇和一罐干瘪的梅干。 他没叫过人,嘴里念叨的也不是病,而是“铜鼓岭”和“后街豆腐摊”,那些他年轻时跑过、吃过的地方。 医生说他迷糊了,但护士听懂了,说那声音里,有风。 他走得安静,像是怕惊动谁。屋外天刚亮,贵阳的老城区响起第一声鸟叫。 街那头,槐树叶子哗啦啦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