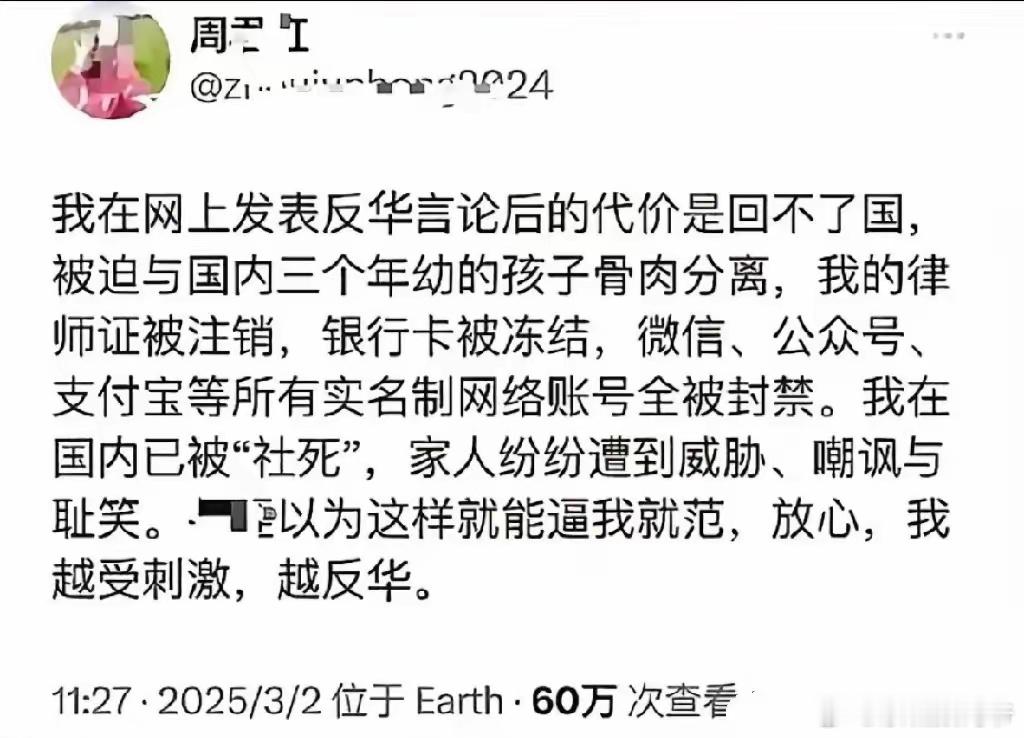1922年,面容清秀的女子身裹破旧的的棉袄饿死在路上,在她弥留之际,映入眼帘的是很多外国人对着她拍照,她奋力张开嘴巴似乎要说些什么,但奈何饥饿让她没能说出最后一句话。本想“善良”的洋人会给口吃的,哪成想洋人只是来拍照的,用他们以为的“趣味”来换取金钱,“善良”的洋人拍完照,迈着绅士的步伐扭头就走了。 1922年,一个面容清秀的女人,裹着破棉袄饿死在路上。快不行的时候,她看见好几个外国人端着相机对着她。她拼命张开嘴,想说点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她可能以为这些“文明人”能给口吃的,结果人家只是来“采风”的。拍完照,那些“善良”的洋人,迈着绅士的步子,扭头就走了。 这张照片背后,是一个被“观看”的死亡,和一个被彻底无视的灵魂。 每次想到这个画面,脑子里总会跳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对,就是写《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个茨威格。一个是中国路边的饿殍,一个是维也纳痴情的女人。琢磨一下,那个陌生女人,用一辈子去爱一个作家,为他生孩子,为他堕入风尘,可到死,那个作家都没认出她是谁。她在他眼里,不过是无数个露水情缘里,一张模糊的脸。 她用尽一生,写下一封长信,开头就是:“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一生,它是属于你的,而你却从不知情。” 1922年那个死在路上的女人,她没能写下信,没能说出话。但她的一生,同样属于那片她热爱的土地,而那些用镜头记录下她生命最后一刻的人,对她的一无所知,并且毫不在意。她,是我们整个民族历史深处,一个沉默的“陌生女人”。 1922年。那会儿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尤其是华北地区,刚经历了1920到1921年的特大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史书上冷冰冰的几个字“华北五省大饥荒”,背后是至少1000万人的死亡,和3000万等待救援的灾民。 1922年,灾情的影响还在。很多人以为饥荒就是没粮食吃,其实它像一场海啸,过去了,留下的也是一片废墟。土地荒着,经济垮着,人也散了。无数人背井离乡,一路乞讨,一路倒下。标题里那个女人,就是这千万分之一。 她可能叫翠花,也可能叫兰香,她有过爹娘,或许还有过丈夫和孩子。她可能也曾坐在炕头上,纳着鞋底,盼着来年的收成。但在那个时代,个人的努力,在天灾人祸面前,脆弱得就像一张纸。饥饿让她走上逃荒的路,也把她生命的终点,定格在了这条冰冷的路上。 这时候,那些外国人登场了。 当时确实有很多国际组织和外国友人在中国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筹款筹粮,功不可没。但,也存在着另一群人。他们是记者、是探险家、是游客。在他们的认知里,古老、贫穷、挣扎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奇观”。 他们带着一种猎奇的心态,把镜头对准了这片土地上最触目惊心的苦难。灾民、乞丐、裹小脚的女人、抽鸦片的男人……这些都成了他们眼中“有趣”的东方素材。这些照片传回西方,满足了那边民众对遥远国度的想象,也为拍摄者换来了名誉和金钱。 当一个人把另一个活生生的人,尤其是一个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当成一个“素材”的时候,他已经抽离了最基本的人性。那个女人在弥留之际,奋力张口,那是一个生命最后的求救信号。她看到的,是相机冰冷的镜头,和镜头后那双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兴奋的眼睛。 那咔嚓一声,不是记录,是掠夺。 它把一个人的死亡,变成了一张可以贩卖的奇闻。而拍完照,他们“迈着绅士的步伐扭头就走了”。这个细节,简直是神来之笔。它写尽了那种文明外衣下的冷漠和傲慢。他们没有弄脏自己的皮鞋,没有伸出援手,甚至可能都没有一丝的愧疚。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然后心安理得地去往下一个“景点”。 1922年的那条路。那个女人,她最后想说什么? 她可能想说:“行行好,给口水喝吧。” 她可能想喊出自己孩子的名字。 她甚至,可能只是想用最后的力气,咒骂这个不公的世界。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她的声音,和她的生命一起,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茨威格笔下的陌生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选择用一封信,呐喊出了她一生的爱与痛。她让那个男人,也让所有读者,终于“看见”了她。她的死,因为这封信而有了回响。 而我们故事里的这个“陌生女人”,她的存在,只剩下一张可能流传于世的照片。她成了历史的一个符号,一个注脚,一个用来控诉帝国主义和旧社会黑暗的“道具”。很多人会义愤填膺地讨论这张照片,但很少有人会去想,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一生是怎样的。 她被看见了,但她从未被理解。



![长征九号距离立项还远么[doge]](http://image.uczzd.cn/257953874711806718.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