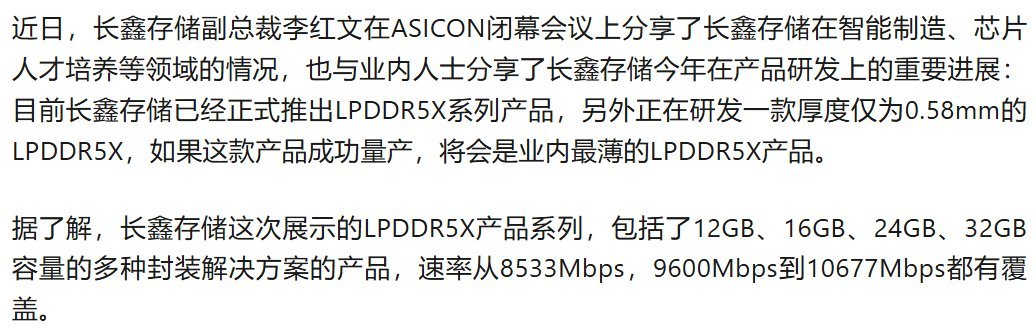2007,钱学森96岁的庆宴上,穿过数以百计的宾客,站在一位女士眼前。他颤着声,“你...还好吗?”钱老激动的握住女人的手,“你现在还有几个孩子?”那女人却平静的回答,“一个都没有了。” 中国科技大学档案室里,一本 1978 年的英语教材静静躺着。 扉页 “李佩” 二字边角起皱,夹着张泛黄纸条:“今日化疗,教材改日再校。” 这是她女儿郭芹患癌时,她边陪护边编写的教材,从没人知道。 档案管理员轻轻翻开,每页都有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墨迹还带着温度。 2007 年钱学森庆宴上,90 岁的李佩被钱老握住手时,口袋里正揣着这教材的再版校样。 “你还好吗?还有几个孩子?” 钱老的关切像暖流,却让她想起女儿与丈夫。 “一个都没有了。” 她平静回答,指尖攥紧校样,没提教材,也没提那枚烧黑的手表残片。 满堂寂静里,没人知道她刚熬夜改完教材,眼里的红血丝藏着半生的失去与坚守。 1968 年 12 月,郭永怀飞机坠毁的消息传来时,李佩正在给学生上英语课。 课后,工作人员把烧黑的眼镜片和手表残片交给她,她摩挲着残片边缘,没掉一滴泪。 当晚,她打开丈夫的书桌,将散落的科研手稿一张张整理平整:“这些是国家的宝贝,不能丢。” 接下来半年,她每天下班后研读手稿,遇不懂的航天术语就查资料、问同事,还把关键内容抄进笔记本 —— 后来这些都成了教材里的鲜活案例。 1970 年,学校开设航天英语课程,李佩主动请缨授课。 她把丈夫手稿里的术语融入教案:“这些词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报国心。” 学生问起术语由来,她只说 “是一位前辈的研究”,从不提 “郭永怀” 三个字。 直到多年后,学生们在博物馆看到郭永怀的手稿,才懂她课堂上的深意。 1976 年,李佩接到编写研究生英语教材的任务,女儿郭芹刚查出癌症。 她白天去学校搜集资料,晚上趴在医院病床边写教材,手边放着丈夫的笔记本。 郭芹疼得睡不着,她就边揉腿边念教材初稿,偶尔讲丈夫的科研故事:“你爸爸搞研究时也这么较真。” 女儿笑着夸 “妈妈写得好”,她却转身擦泪,怕自己绷不住。 这本教材前后改了 12 稿。有次校样送晚了,她冒大雨骑车去印刷厂,车翻在泥里,先护着校样和笔记本,自己浑身是泥却浑然不觉。 “这教材关系到学生的前途,不能耽误” 她跟印刷厂师傅说,声音发颤。 1978 年教材出版时,郭芹化疗刚结束,她把第一本送女儿,第二本放丈夫书桌前:“算咱们仨一起完成的。” 1981 年,李佩和李政道合作 CUSPEA 项目,发现农村学生张磊英语基础差。 她每天下班后给张磊补课,用丈夫的笔记本当教具:“结合实际研究记术语,才好懂。” 她没跟同事提补课的事,也没说笔记本的来历,只说 “这孩子肯学,别耽误了天赋”。 后来张磊留学美国成了量子物理专家,2008 年听说李佩捐 60 万设奖学金,立刻捐 100 万要求以 “李佩” 命名。 李佩却悄悄跟学校说:“别提我的名字,要提就提‘科研前辈’,是他们的精神在帮人。” 1996 年郭芹去世后第七天,李佩提着录音机去上课,包里藏着女儿的照片和丈夫的笔记本。 课前她在走廊偷偷看眼照片、摸下笔记本,把思念压在心底,走上讲台依旧精神饱满。 讲到 “爱国” 时她突然停顿:“这个词要记在心里,像前辈们那样用行动去做。” 学生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是女儿的 “头七”,她口中的 “前辈” 就是郭永怀。 2010 年,89 岁的李佩还在给学生改论文,眼睛花了就用放大镜,手边始终放着那本笔记本。 有学生的论文涉及航天英语,她翻出笔记本:“你看这个术语,当年你郭叔叔这么翻译更准确。” 学生在论文致谢里写 “感谢李老师,感谢郭前辈的精神传承”,她没让删,只轻声说:“把传承继续下去。” 如今,1978 年的英语教材已再版 18 次,帮助了数十万研究生;郭永怀的手稿被整理成册,放在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供学生查阅。 张磊设立的 “助学基金”,每年资助 50 名农村学生,已有 300 多人考上大学,不少人选择了航天、物理专业。 教室里,常有老师拿着教材和手稿说:“这是最珍贵的教学资源,是精神的接力棒。” 李佩的墓碑前,每年都有学生、老师和航天科研人员前来。 有人捧着科研报告,有人拿着教材,轻声说:“李老师,郭先生,咱们的研究又有新突破了。” 风拂过墓碑上 “怀瑾佩瑜,师表后继” 八个字,仿佛在回应:她和他从未离开,他们的精神藏在教材里、手稿里、学生的成长里,藏在每一个为国奉献的身影里,永远活着。 主要信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佩:传播爱与智慧 在奉献中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