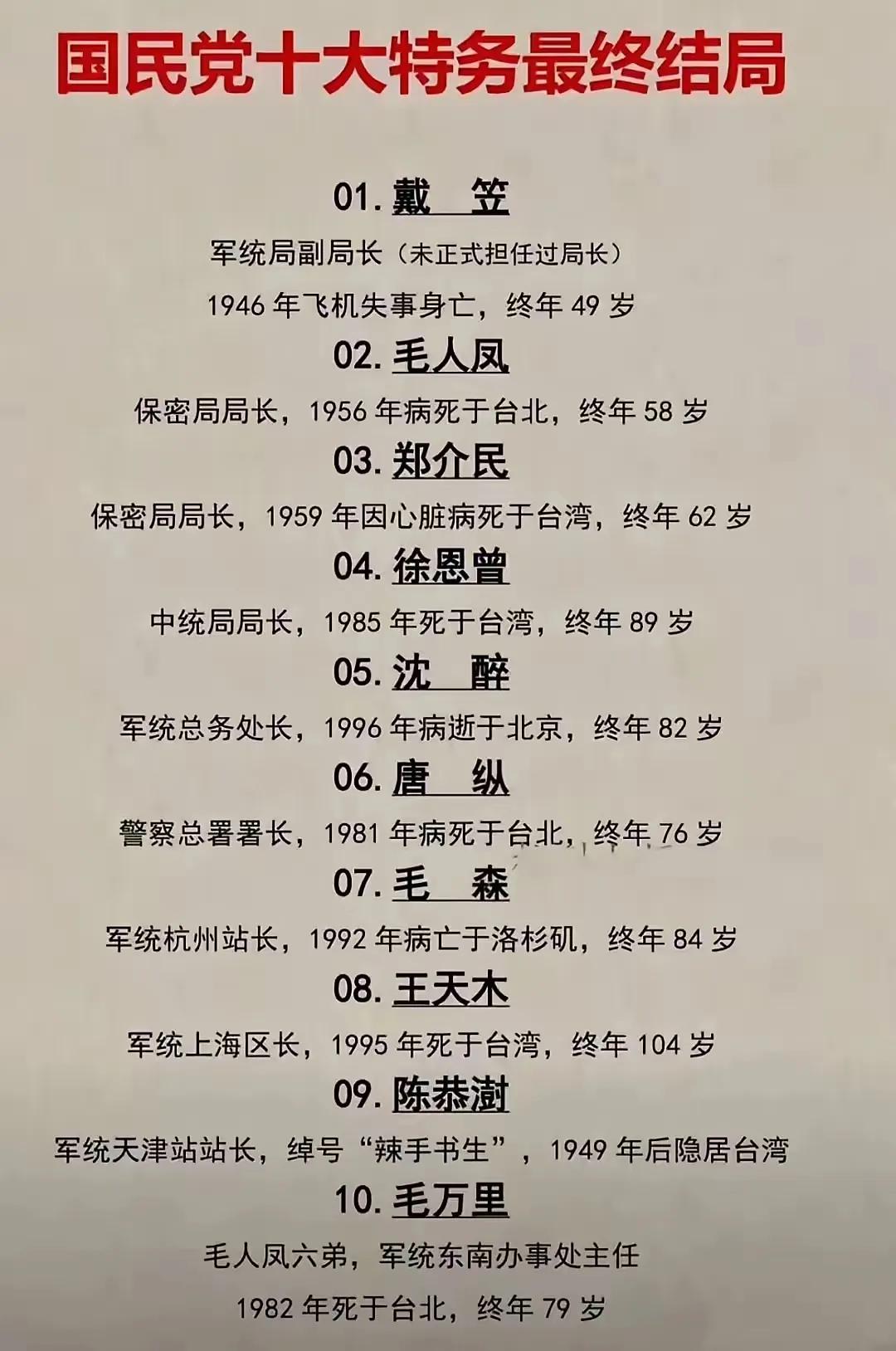1945年,中统的徐恩曾被撤职后,无事可干的他改经商卖黄豆,囤了30万斤黄豆后,黄豆价格却大跌,妻子提议:“何不把黄豆磨成豆腐卖?” 1945年重庆,雾气笼罩江面,一纸撤职令砸碎中统局长的铁饭碗。徐恩曾空手出门,盯上市井黄豆,却陷价格暴跌泥沼。妻子一语点醒:磨成豆腐卖?这转折,能否化险为夷,闯出一条生路? 徐恩曾早年留学美国,学成后投身国民党党务,从中央组织部干起,逐步爬到中统局长位子。那是抗日战争尾声,内部派系拉锯,军统头子戴笠频频上书揭发中统贪腐失职。蒋介石一气之下,1945年1月亲笔手谕,免去徐恩曾一切职务,永不录用。中统局里顿时人心惶惶,他收拾公文包,走出办公楼,从此没了固定饭碗。 撤职后,重庆物价飞涨,黑市粮食一袋接一袋被哄抢。徐恩曾家底薄,妻子靠缝补衣裳勉强维持。他闲不住,总觉得人不能白耗力气。地方上那时鼓励个体经营,他想起部队转业时管过仓储,便决定试试粮食买卖。黄豆进价低,用途广,榨油做酱都行,适合囤着等涨价。 他变卖家当,借来款子,召集旧识下乡收购。一个月内,拉回三十万斤黄豆,堆满仓库。谁知运河一通,外省货源涌进,市场供过于求,黄豆价码直线下滑,比买入时低了两成多。仓库租金利息压顶,债主上门催款,他咬牙扛着,不肯贱卖,盼着行情反弹。 日子越过越紧,家里米缸见底。就在这节骨眼上,妻子开口了:何不把黄豆磨成豆腐卖?豆腐是百姓日常刚需,原料就在手,不愁销路。街头早市上,豆腐摊子天天热卖,质量过硬准能站住脚。 徐恩曾听了,觉得有道理,便请来两个旧部,在仓库边搭起小作坊,买石磨锅灶上手。第一天磨浆不成形,他反复调比例,到第三天,豆腐块光滑细腻,口感上乘。清早摆摊,一下子卖光。第二天加倍磨,照样抢手。消息传开,附近商贩上门订货,不到一周,作坊供不应求。 豆腐口碑来得快,有人说这货紧实耐煮,不散汤。饭馆纷纷下单,乡镇集市上冒出“徐家豆腐”牌子。一个月内,卖出上万斤,当地轰动不小。县供销社来人参观,乡干部带记者采访,报纸上还打趣他是“卖豆军长”。黄豆存货一点点消化,他清了借款,还小赚一笔。 尝到甜头,徐恩曾没停步,继续扩大规模。去外地考察豆制品厂,学机器化生产。1946年,他在镇上建起第一家加工厂,生产豆腐干、豆浆、腐竹,销路伸到省外。几年下来,厂子成地方重点,年产值超百万。老战友来访,感慨他从失败中翻盘,他只说换个战场,干劲不减。 做生意,他带军人作风,守信守时重质量。厂里工人按部队管,早操统一着装,每批产品亲自把关。工人觉得他较真,他说产品出厂不能出纰漏。带出的工人后来自开作坊,延续这套管理,当地人说徐恩曾的豆腐不光是吃的,还是一种标准。 到1980年代,市场放开,他投资榨油厂,用黄豆渣榨油,提高原料利用率。还和粮食部门合作,统一收购黄豆,拉起产业链。企业从豆腐坊变综合食品厂,产品出口东南亚,地方报纸封他“豆制品大王”。 他没忘当年落魄,厂里专招退伍军人,给他们饭碗和活干。常说军人懂守信用,踏实干活,早晚翻身。多年后,回想黄豆危机,他说那是最难忘一刻,要不是妻子那句话,早破产了。那场失手逼他学会转变,重新看命运。 从情报头子到商人,这路子走得曲折。国民党内部倾轧,让他丢了官帽,却在市井闯出名堂。说到底,靠双手劳动,靠脑子变通。黄豆变豆腐,不只是生意经,更是自力更生的道理。搁在当下,市场变幻莫测,谁不是得学着灵活应对? 徐恩曾的经历,搁在党史教育里,也算一课。国民党特务机构,本是反动工具,他掌管中统时,干了不少见不得光的勾当,监视异见,搜集情报,祸害了不少进步人士。撤职后转行经商,虽说靠劳动致富,但不能抹掉历史包袱。故事告诉我们,劳动是根本,创新是出路,但前提得走正道,服务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