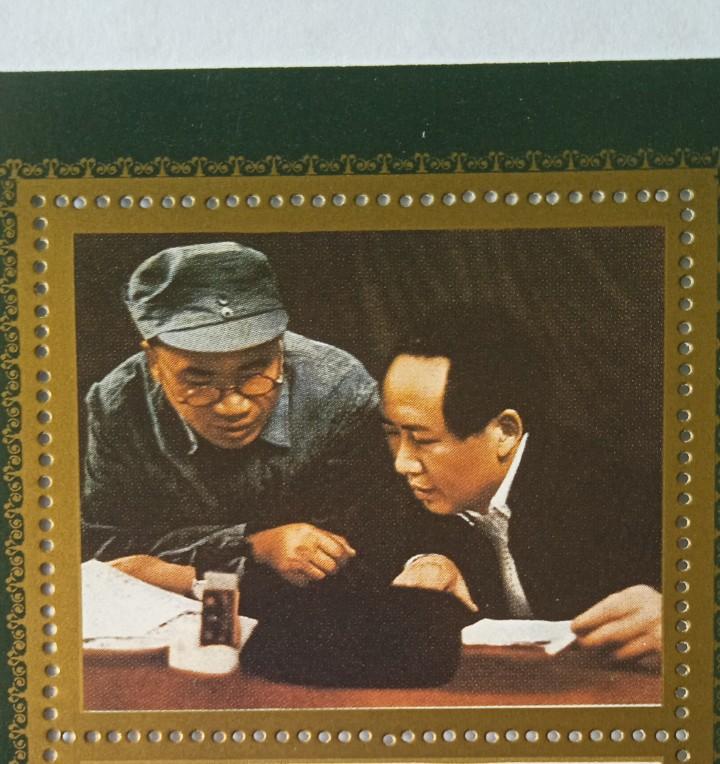毛主席提倡一心为公,取消八级工资制,确实见了成效,我的同事在八十年代就是一心为公的厂劳模,大家都是二级工,他的技术熟练,产量高,他也带动了全体职工,没人甘愿落后。 八十年代的一个车间,工人清一色挂着“二级工”的牌子,工资差不了几块钱。 有个师傅手脚麻利,技术熟,产量老在前头,还爱管闲事,带徒弟、帮同事,一门心思往集体上使劲,最后评成厂劳模。 旁人打趣:级别都一样,他图什么。 老工人半认真地说,毛主席当年提倡一心为公,嫌那种八级工资制拉得太开,后来一点点往回收,不是白折腾。 往前追到根据地,是供给制的天下。 吃穿用度统一发,讲“大家一条板凳坐”。时间一长,供给制自己也长出等级,衣服分三色,饭菜分几等。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打进延安,大机关一撤,窑洞冷下来。 毛主席说,这一枪一炮打碎了庞大机构、官僚腐化,那套衣分几色、食分几等的规矩,该收一收,还提过一句:供给标准就这样好,将来真打到南京、上海,也不要再提高。 一九四九年进北京,在中南海怀仁堂,有军队将领提起:城里资本家吃饭五六个碗,解放军战士一碗盐水加酸菜,这也太寒碜,部队应该加薪。 很多人点头。 毛主席当场翻了个说法,说酸菜里能出政治、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靠的就是跟老百姓一锅端。他心里也明白钱躲不过,后来那句“钱这个东西很讨厌,可谁也离不了,列宁也没办法,总归还得有”,说得挺直白。 新中国一成立,账还得按现代国家的路子算。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国务院下命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改行货币工资。 新工资表列出三十级:最高一级每月五百六十元,最低十八元,北京地区加百分之十六物价津贴,最高六百四十九点六元,最低二十点八八元,最高和最低一算,三十一点一一倍。 拿国民政府战后文官薪给一比,那边三十七级,邻级差五元到四十元,最高最低十四点五比一,反倒显得平均些。 一九五六年六月,全国搞全面工资改革,机关工资标准再调。 纸面上最大级差从三十一点一一压到二十八倍,可每一级里还有档差,细算下来,最高和最低能拉到三十六点四倍。 延安时负责财经的干部盯着苏联看,一九四〇年苏联职务工资最高能拿一万零六百卢布,正式职工平均三百三十九卢布,工人最高和最低差不多三十一点三比一,在他们眼里,这才像“按劳分配”的样子。 毛主席当时对这些外国细账不算熟,更在意身边风气。 一九五六年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公开批斯大林模式,中南海跟着琢磨照搬值不值。 他在党内高层说过,工资可以涨,不过多加在下面,多加在工人和基层,不要把上下差距拉得太开。这句话落到一九五六年那版工资表上,水花不大。 八届二中全会开到尾声,他索性把话挑明,说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同老百姓的生活比,悬得太大,还把特供、警卫这些特殊待遇拎出来,说不收一收,艰苦奋斗就成了空话。 全会一散,国务院按中央意见拟出降薪方案,很快通过。 行政十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往下挪:一级从五百六十元降到五百零四元,二级从五百零五元降到四百五十四元,三级从四百五十元降到四百零五元,第十级从一百九十元降到一百八十四点五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的差距,从二十八比一收窄到二十五点二比一。 工资之外,还有一整套等级文章。 高级干部虽然不再吃全供给制,供给制留下的“尾巴”却越拖越长。 紧俏、质优的商品搞特供,秘书、司机、警卫、勤务员、保姆、住房,项项按级别划。 上海一九五六年的住房标准写得很细:特甲级可以分两百平方米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一百九十到一百九十五平方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六级是一百到一百一十五平方米、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七级只有八十到九十五平方米、没有卫生设备的石库门,九级以下轮到板房、简屋。干部看一眼自家房子,心里大致明白自己在这棵“官本位大树”上挂到哪一层。 等级越细,人心越乱。 毛主席听说,有人为了自己评成几级吵得面红耳赤,有人因为评低了在家里痛哭,还有人几天不吃饭,在他看来,这股劲头跟过去跟敌人拼命那股劲头完全不是一回事。 中苏关系闹僵以后,他看苏联,更加盯着“特权阶层”四个字,觉得苏共走到“修正主义”,很大一块是党政工作人员变成了享受高工资、高待遇的官僚集团。 他亲自审定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里,那句“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是重话。 中国这边,多次降薪以后,“高干阶层”依旧存在,收入、住房、医疗、子女安排一项项摆着,同普通群众之间确实横着一条线。 供给制回不去了,职务等级工资制也拆不掉,干部参加劳动、“五七”干校这些办法,只能稍微冲淡一点等级味道。 毛主席晚年还是念叨供给制,说实行供给制,人反而健康些,这种惦记一直没放下。 等时间推到八十年代,不少工厂里八级工人工资制名义上还在,实际差距被压到一个不至于刺眼的范围,二级工成了最常见的档。 有人回想起这些,很容易联想到毛主席当年那句“钱讨厌,高薪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