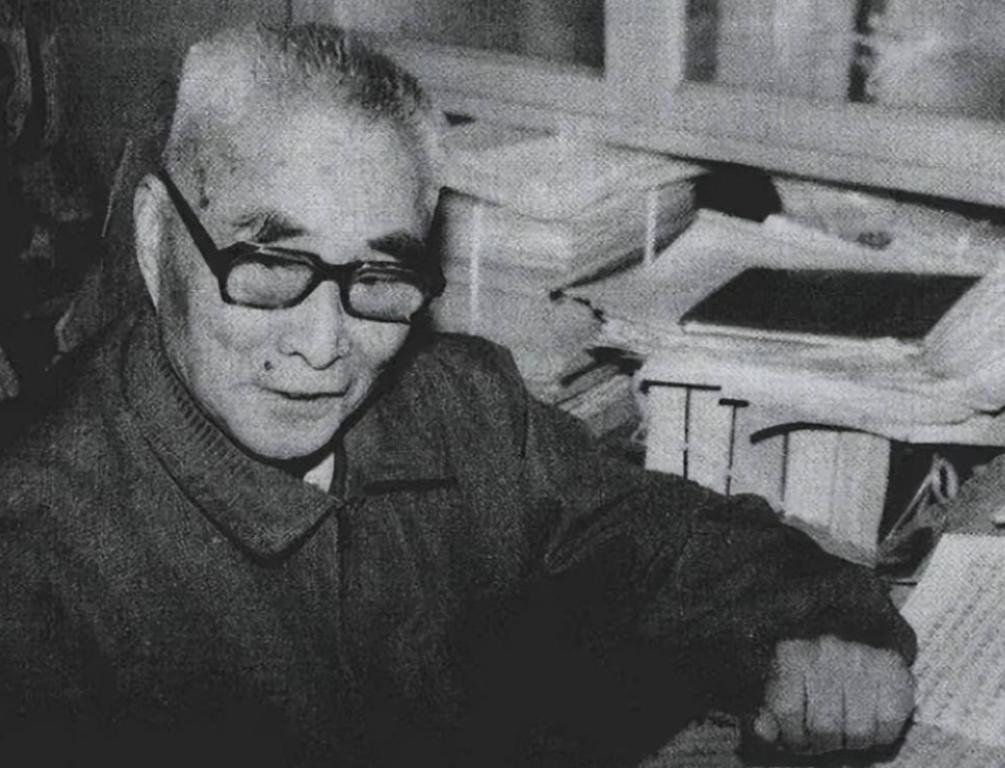1949年10月初,马步芳逃到台湾后,蒋介石以“擅离职守”撤了他所有职务。马步芳自知在台湾已无立足之地,以三千两黄金贿赂几个大员,取得了离台手续。 兰州战役前,蒋介石刚把马步芳提到陆军上将,指望这支西北军顶在前线,结果枪声一响,父子俩先走一步,部队丢在身后。很快,“擅离职守”的处分从台北下达,之前所有官衔一扫而空,昔日马家大帅瞬间变成被弃用的老兵。 没有兵权,也没有官职,台湾对马步芳来说不是避风港,反而像随时会合帐的囚笼。他很快判断,唯一出路就是再逃,而且要逃出蒋介石伸手够不到的地方。 那时想离台谈何容易,更别说这种重点人物。马步芳照旧用金子开道,托人找到吴忠信等蒋介石身边红人,送上三千两黄金,只提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去麦加朝觐。 这层宗教外衣既体面又难以挑刺,配合金子的分量,离境批文终于签下。马步芳立刻包了三架英国客机,带着家眷部属飞往沙特,中途在开罗买楼开舞厅、办旅馆,自以为从此可以在中东重做土皇帝。 换了地理位置,旧习一点没改。青海积累的巨额财富,支撑他在埃及和沙特继续奢靡,舞厅夜夜笙歌,华侨生意人被层层盘剥。权力和金钱垒高,欲望就彻底失控,那句“除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的狂语,并非夸张,而是日常。 在青海,下属妻女、宗族姊妹、侄女侄媳,不少人都成了受害者。到了中东,身边姨太太成群,连去麦加朝觐都要带着一队女人,惹得当地阿訇当场怒斥,差点以人口贩卖论处,马步芳只好暂时把姨太太们“拆散寄存”,等仪式结束再一一收回,成了当地茶余笑柄。 真正把这份恶名撕开给全世界看的,是马月兰。这个堂弟马步隆的女儿,年仅18岁,长相俏丽,又熟练掌握阿拉伯语。 马步隆以为投靠堂兄能多一条生路,马月兰却在“安排工作”的名义下被接入公馆,白天捶背唱歌,夜里被灌酒下药,醒来时已经成了马步芳掌控下的“姨太太”。 在威胁“全家都别想活”的恐吓下,父亲只能吞血认命。 1957年,马步芳再拿出一万两黄金替蒋介石祝寿,顺势接了台湾驻沙特大使的头衔。以那点文化水准,大使馆公文大多只在纸角签个“阅”,真正用心经营的是大使公馆里的后院人生。 权力一抬高,欲望又向更近的血缘伸过去。马步芳不仅逼马月兰公开以姨太太身份出现,还打算把马月兰的母亲和两个未成年妹妹一起接入公馆“共同生活”,母女姐妹共侍一人的畸形构想,将这个原本逆来顺受的侄女逼到绝境。 1961年,长期压抑终于爆炸。马月兰抓住缝隙,从大使馆逃出,躲进台湾驻沙特外交官宋选铨家中,请求帮助回台,同时向台湾有关部门密集递交检举信。 马步芳得知后气急败坏,带着手下围住宋家要人,甚至威胁“不给人就拿你女儿顶上”。在屋里听到这句话,马月兰不忍恩人受牵连,走上阳台,当着越来越多的围观者,用中文和阿拉伯语把多年遭遇一条条抛向街头。 从强迫十八岁侄女为妾,到打算逼十五岁妹妹一并嫁入,从在青海的肆虐,到在中东华侨中的盘剥,这些原本被锁在高墙内的秘密,被她用最直接的语言吼给了上百名记者和各国外交官听。 懂阿拉伯语的人当场翻译,很快聚集了八百多人,连周边道路都堵死,这场原本被马步芳定义为“家务事”的争执,瞬间升级为跨国外交丑闻。 沙特外交部门不得不出面,台湾方面也顾不上遮掩,先把马月兰护送回台。当地华侨趁机联名控诉多年被压榨的经历,台湾报纸则用“风流大使太荒唐”“侄女充姨太”等刺眼标题连日追踪,舆论汹涌之下,当局只能撤销马步芳大使职务,下令回台受审。 马步芳干脆辞职,拒不踏上归途,躲在沙特公馆里苟活。昔日“西北狼王”,最后成了在沙漠边缘抱着旧日财物过日子的孤老。 1975年夏天,七十二岁的马步芳在沙特病死,没有等到“叶落归根”,也没有机会在权力场上翻篇,只留下那场阳台风波里侄女撕心裂肺的控诉,和一地被风沙掩埋的民脂民膏。 从西北临阵脱逃,到海外侄女当众揭丑,马步芳一生,把军阀身上那层伪装的“忠义”彻底撕碎。枪口可以压住一时的沉默,却挡不住迟来的围观与声讨,他想用黄金买来的出路,最后只换来一纸耻辱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