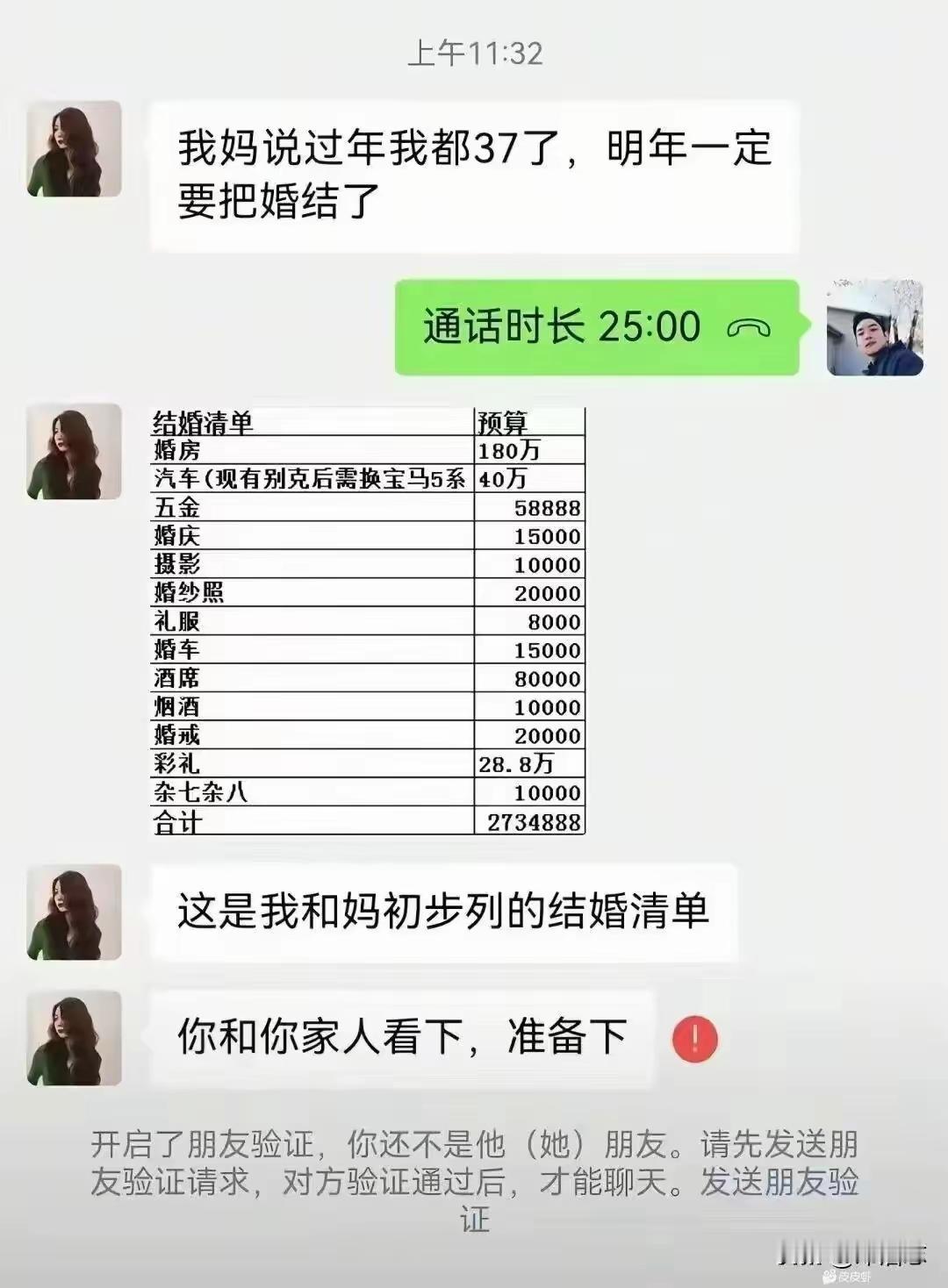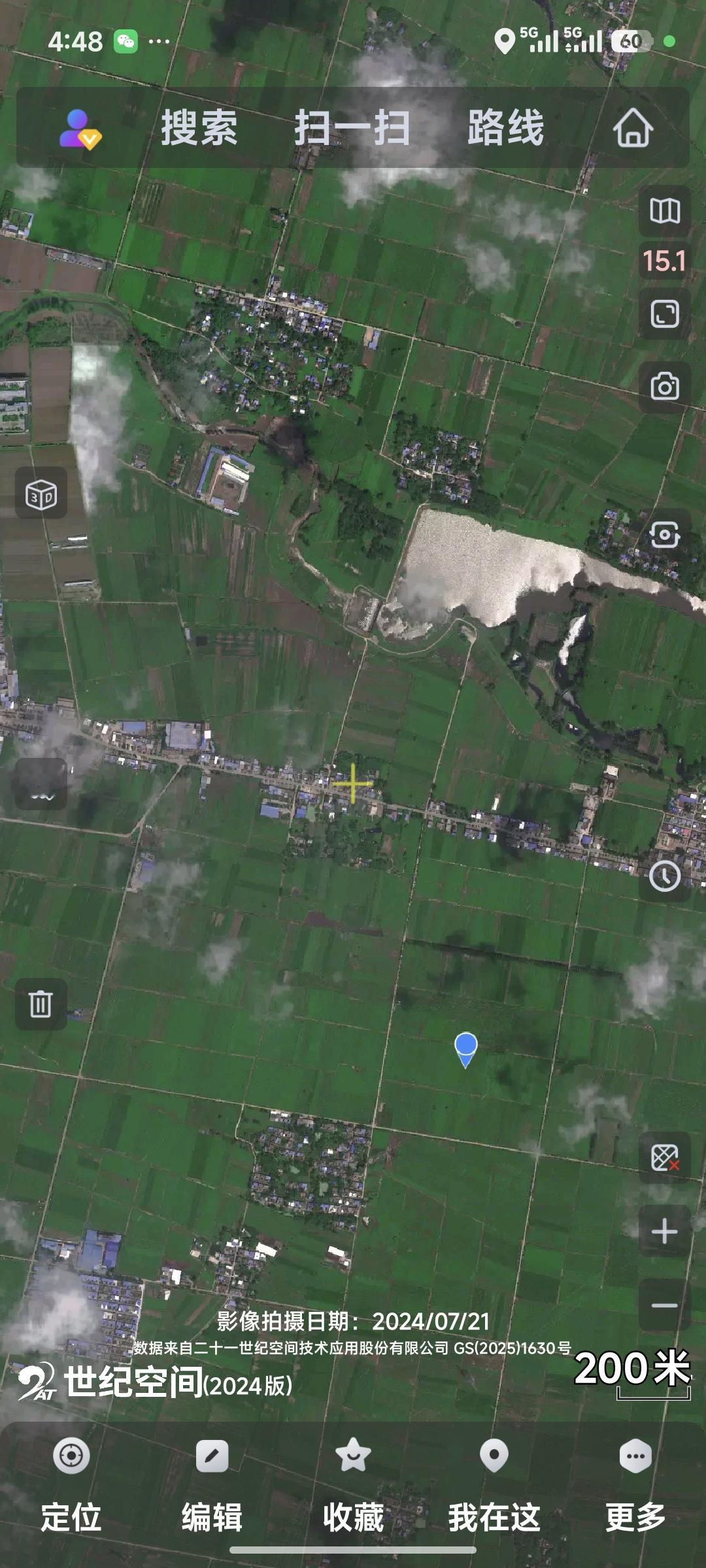这是九十年代曾志来到农村看望自己的长子石来发。此时,石来发早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当他初次看到几十年未见的母亲时感觉不到母子之间的亲情,而更多的是母子之间的陌生感。 眼前的老太太,衣着整洁,气质和这小山村格格不入。石来发搓了搓那双布满厚茧、沾着泥星子的手,喉咙里像堵了团干稻草,那句“妈”怎么也喊不出口。他记忆里没有母亲确切的样貌,只有邻里长辈偶尔提起的零星片段,拼凑出一个模糊又遥远的影子。如今影子变成真人站在跟前,除了局促,他心里空落落的,泛不起一点应有的温热。老太太看着他,眼神复杂,有关切,有愧疚,或许还有些他看不懂的沉重。两人就隔着门槛站着,夏日的风穿过堂屋,带着燥热,却吹不散那份厚重的生疏。 这能怪谁呢?石来发很小就知道,自己是“送给”这里人家的孩子。养父母是厚道的庄稼人,待他如亲生,省下口粮供他读了几年书,更多的时候是教他扶犁、插秧、辨识天气。他的根,早就扎进这片红土地里了。生母曾志,那是了不起的人物,是干革命的。革命意味着颠沛流离,意味着枪林弹雨,也意味着骨肉分离。为了那个更大的信念,她当年不得不做出选择,将襁褓中的长子托付给井冈山脚下的老乡。这一别,就是几十年。石来发的人生轨迹,和母亲从此天各一方。他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娶妻生子,计算着粮价和收成;母亲则在历史的洪流里起伏,肩负着她的使命与责任。两条线,平行了半个多世纪。 突然有一天,线要交会了。消息传来,说母亲要来看他。石来发一宿没睡,蹲在门槛上抽了一夜的旱烟。他心里乱。按理说,该高兴,该激动,那是生你的娘啊。可他就是高兴不起来。养父母前些年相继过世了,他披麻戴孝,摔盆打幡,哭得真切。那份养育之恩,实实在在,沉甸甸地压在他心里。现在突然来了位“母亲”,他该用什么表情去面对?用对待养父母那份亲昵?他做不出。用对待远客那份客气?那更不对味。这份血缘带来的不是亲切,反而成了一桩沉重的心事,压得他喘不过气。 见面那天,村里不少乡亲远远看着。他们看见那个城里来的老太太,也看见他们熟悉的、老实巴交的石来发。两人坐在屋里,话很少。曾志问起他的生活,问起他的孩子,问起地里的收成。石来发回答得简短,一问一答,像汇报工作。他偷偷打量母亲,试图从那张满是风霜却坚毅的脸上,找到一丝和自己相似的轮廓。找到了,心里却更茫然。这份相似,除了证明生物学上的关联,还能证明什么?几十年的光阴,是实实在在的鸿沟,里面填满了彼此完全缺席的岁月。他童年摔跤时,渴望的怀抱不是她的;他成家立业时,期待的叮嘱也不是她的。缺失了共同经历的血缘,薄得像一张纸,一阵风就能吹破。 曾志心里想必更不是滋味。她为革命付出了一切,这“一切”里,就包含了难以估量的个人情感,包含了做母亲的天伦。她看到儿子那双和自己年轻时有些相像的眼睛,看到他被生活磨砺得粗糙的皮肤,看到他身上洗不去的泥土气息。这气息,本不该是她儿子全部的人生底色。愧疚像细密的针,扎在心上。她想补偿,可怎么补?缺席了几十年,不是给些钱、带些东西就能填平的。她给不了他童年,也给不了他那些他早已习惯、并深深融入的田间日常。她能给的,或许只剩下这份小心翼翼的、带着距离的探望,和一份永远无法说出口的抱歉。 这次见面,没有抱头痛哭的戏剧场面,只有弥漫在简陋农舍里、几乎令人窒息的沉默和尴尬。坐了一会儿,石来发站起身,说要去看看田里的水。曾志点点头。他走出门,走进灼热的日光里,走进他熟悉得如同身体一部分的田野。泥土的气味包裹着他,让他稍稍平静下来。田埂上,他的儿子,一个半大少年,正光着脚丫追蜻蜓。石来发看着儿子,心里忽然一阵酸楚,又一阵明晰。他错过了母亲的陪伴,但他发誓,绝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再经历这种血缘上的“陌生”。有些分离,是时代洪流下的不得已;而有些相守,是平凡人能够牢牢握在手里的全部。 这次探望后,曾志离开了。石来发的生活恢复了原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村里人偶尔还会提起,说石来发有个了不起的母亲。石来发听了,只是笑笑,继续侍弄他的庄稼。那段被时代割裂的亲情,如同断了的风筝线,知道它在那里,却再也接不回去了。它成了一段隐秘的家族记忆,一份深藏于时代褶皱里的个人悲欢,不激烈,不渲染,却沉重地诠释了“奉献”二字背后,那些具体的人所承受的、具体而微的代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