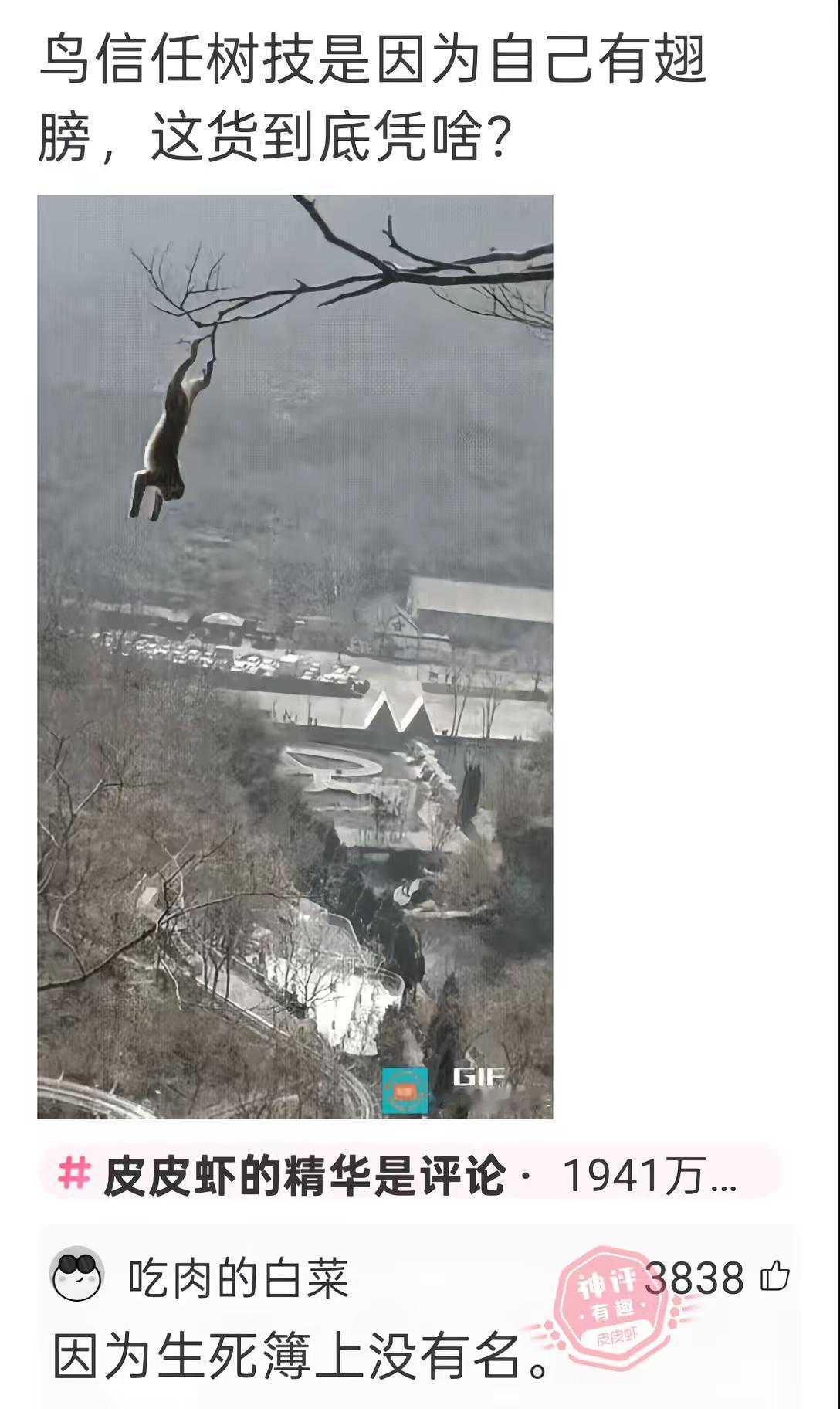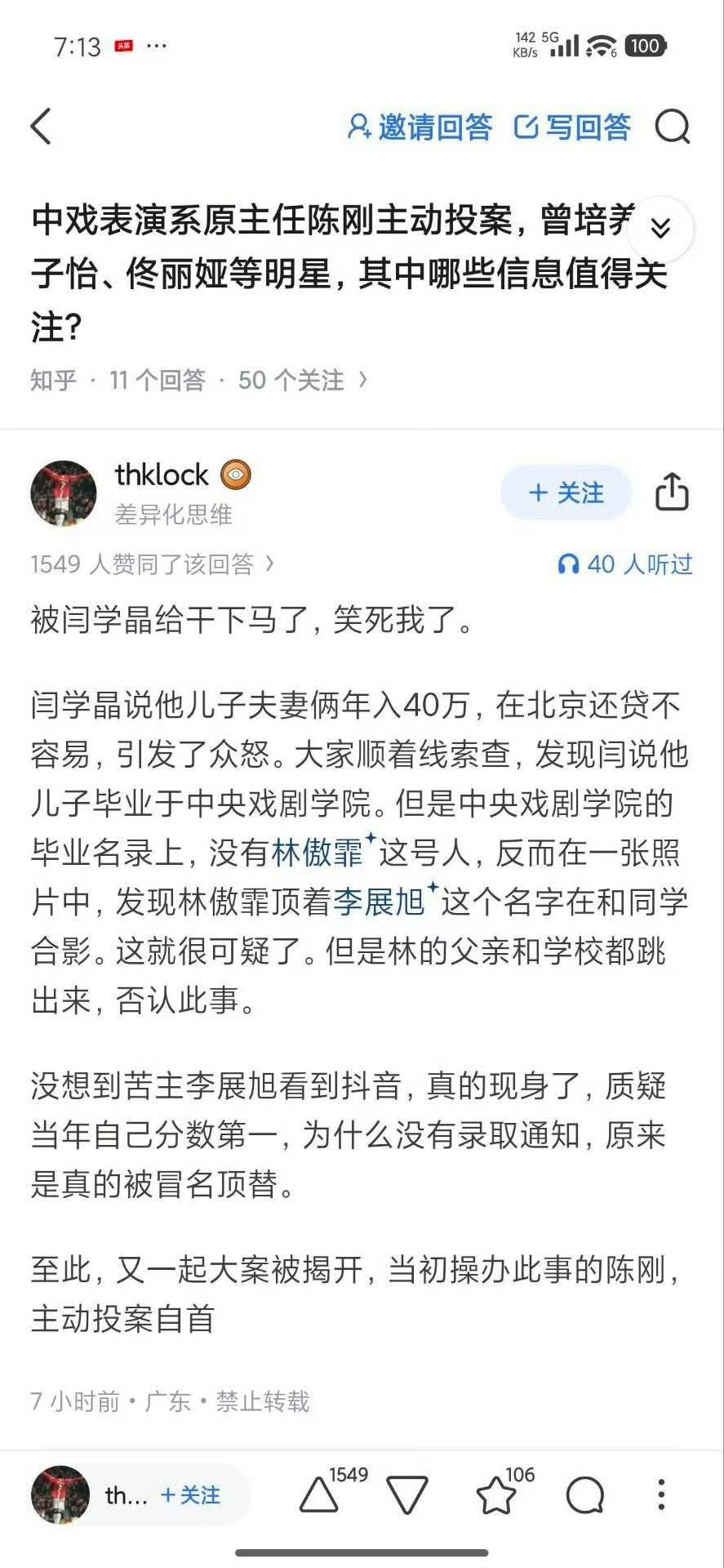我爱上了一个在云南徒步时救我的彝族男人陈默。
导游林月哭着阻拦我:“他是‘天菩萨’,你嫁给他会死的!”
我不听劝,执意要嫁。
婚礼前夜,林月再次哀求:
“我姐姐就是嫁给了上一任天菩萨,新婚夜之后就疯了!”
新婚夜,我被带进一间贴满神像、弥漫药香的房间。
7位毕摩围坐火盆,诵经声低沉如地底传来。
陈默被蒙眼坐在中央,白袍被缓缓褪下。
我终于看到了他后背那令人窒息的东西。
01
我双膝发软跪在地上,眼前的景象让我几乎窒息。
七个身着深色法衣的毕摩围坐在火盆边,炭火烧得通红,那把银刀在火焰中已经变成暗红色。
诵经声低沉压抑,像是从地底深处传来,每一声都敲打在我的心脏上。
陈默被蒙着双眼坐在中央,白布遮住了他大半张脸,我只能看见他紧抿的嘴唇,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七天前,林月也是这样跪在我面前,哭着抓住我的手腕说:“苏晚姐,求你了,现在走还来得及。”
那时候我还能勉强站立,现在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陈默的母亲为我整理嫁衣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她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孩子,无论看到什么都别跑,他需要你。”
我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的重量,直到此刻,我才隐约感觉到,有些真相的重量足以压垮一个人。
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草药味,混杂着炭火灼烧的气息。
墙上贴满了神像,那些神像的眼睛在烛光摇曳中仿佛都在盯着我。
我想起三天前的深夜,林月冲进我暂住的屋子,眼睛红肿得像桃子。
她抓着我的肩膀,指甲几乎要陷进我的肉里。
“我姐姐就是嫁给了上一任天菩萨,新婚夜之后……”她哽咽得说不下去。
停顿了很久,她才用颤抖的声音继续说:“她醒来后就疯了,到现在都不敢靠近火堆。”
我问她到底看到了什么。
林月拼命摇头,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我不能说,提前说了仪式就会失效,他会死的。”
这个“他”指的是陈默。
此刻陈默就坐在我面前,身体在轻微地颤抖,尽管他努力保持着平静。
两个老阿妈走到他身后,她们的手搭在他那件纯白长袍的肩膀上。
白袍的料子很厚,但在烛光下依然能看出他身体的轮廓。
我想起第一次见到陈默的场景,那是在两个多月前,我因为失恋报名参加了云南的徒步旅行团。
当时我根本不会想到,一次散心的旅行会把我带到这里,带进这个满是神像和药香的房间。
02
山体滑坡发生得毫无预兆。
我们一行十二个人正在狭窄的山路上行走,突然就听见轰隆隆的巨响。
碎石像暴雨一样滚落,其中一块足有脸盆那么大的石头直直朝我砸来。
我吓傻了,腿软得动弹不得。
就在那个瞬间,一个身影从侧面冲过来,用力把我推开。
他自己却被石头砸中了肩膀,我听见骨头碎裂的闷响。
那个救我的人就是陈默。
他穿着彝族的黑色察尔瓦,里面的深蓝色马甲绣着复杂的花纹。
血很快浸透了他左肩的衣服,但他还是咬牙背起我,走了十几里山路。
我趴在他背上,能感觉到他每一步都在颤抖,可他的背脊始终挺得很直。
他把我送到村里的老医生那里,自己肩上的伤口缝了九针。
缝合的时候他一声不吭,反而转头问我:“你头上的伤还疼吗?”
他的眼睛很清澈,眼神温柔得像山间的溪水。
老医生说我还需要休养几天,陈默就主动让我住到他家。
他家是传统的木结构房子,建在半山腰上,推开窗就能看见层层叠叠的梯田。
陈默的母亲见到我时,表情有些复杂,欲言又止的样子。
但她还是很热情地招待了我,给我收拾出干净的房间,准备了新的被褥。
住下来的第三天,村里正好过火把节。
陈默带我去村口的广场,巨大的火堆照亮了整个夜空。
年轻人围着火堆跳舞唱歌,气氛热烈欢快。
陈默站在我身边,耐心地给我讲火把节的来历,讲彝族古老的传说。
他的声音很好听,在火光映照下,他的侧脸显得格外好看。
我看着他,心里某个地方轻轻动了一下。
就在这时,林月从人群里冲出来,一把拉住我的手臂。
她的脸色苍白,把我拉到人少的地方,压低声音说:“苏晚姐,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陈默啊,怎么了?”我一脸不解。
“他是天菩萨。”林月的嘴唇在发抖,“你千万别跟他走太近,他碰不得的。”
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
陈默救了我的命,怎么就成了“碰不得”的人?
现在想来,如果那时我能听懂林月话里的恐惧,也许一切都会不同。
但我没有。
我回到陈默身边,他问我林月说了什么。
我摇摇头说没什么。
他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什么,但很快又恢复了温柔。
那天晚上他送我回家,在门口对我说:“明天我带你去山上看看吧,这里的风景很美。”
我说好。
他笑了笑,转身走进夜色里。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03
第二天一早,陈默真的来带我去山上。
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往上走,梯田像绿色的绸缎铺在山坡上。
陈默走在前面,不时回头提醒我注意脚下的碎石。
他的脚步很稳,每一步都踩得扎实。
到了半山腰的草地,他开始采草药,很耐心地教我辨认。
“这是三七,止血用的。”
“这是当归,补血很好。”
“这是天麻,对头疼有帮助。”
他说话的时候手指轻轻拂过草药的叶子,动作温柔得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我看着他的侧脸,心跳不知不觉加快了。
忽然我脚下一滑,身体往旁边倾倒。
陈默眼疾手快抓住我的手腕,但下一秒,他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甩开我的手。
那个动作很大,很慌张。
我愣住了,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他低下头,声音有些发抖:“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
从那次之后,我开始注意到,不管天气多热,陈默都穿着长袖。
袖口的扣子总是扣得严严实实,一点皮肤都不露出来。
有一次我问他:“你不热吗?”
他沉默了一下,轻声说:“习惯了。”
我就没再追问。
在村里住了一个星期,我的伤好了大半,按理该离开了。
但我舍不得。
舍不得这里的宁静,舍不得如画的风景,更舍不得陈默。
那天傍晚,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对他说:“陈默,我喜欢你。”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得让我读不懂。
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才开口:“我也喜欢你。”
但他的声音里没有喜悦,反而像是承认一件极其沉重的事。
第二天我退掉了回程的机票。
但从那天开始,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有人同情,有人好奇,有人一见到我就躲开。
陈默的母亲看到我,眼眶总是红红的。
她拉着我的手想说什么,最后却只是叹气。
我问陈默:“你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
“不是。”他说,“她只是担心你。”
“担心我什么?”
他不说话了,只是看着远处的山峦,眼神沉重。
又过了几天,林月哭着来找我。
她跪在地上拉着我的手:“苏晚姐,别嫁给他,你会后悔的。”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追问。
“天菩萨结婚有禁忌,新婚夜有特殊仪式……”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姐姐就是看完仪式后疯的。”
“什么仪式?”
“我不能说!”林月拼命摇头,“规矩是不能提前说的,否则仪式就无效了。”
“仪式无效会怎样?”
林月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他会死。”
我去找陈默,他正在院子里劈柴。
“新婚夜到底有什么仪式?”我直接问他。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林月告诉你的?”
“她没说清楚,但她说你会死。”
陈默沉默了很久:“我不能说,这是我们彝族的规矩。”
“什么规矩!”我第一次对他发火,“你要我嫁给你,连这个都不肯告诉我?”
“不是不肯,是不能。”他看着我,眼眶红了,“我也不想这样,但这就是规矩。”
他的身体在颤抖,整个人看起来快要崩溃了。
“那你告诉我,如果到时候我受不了呢?”
他沉默了很久。
“那你就走。”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但如果你走了,我就真的没救了。”
我的心猛地一紧。
04
婚礼前七天,我给父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要结婚了。
母亲当场就急了:“你才认识他多久?了解他吗?知道他身体有没有什么毛病?”
我说不出话。
因为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你这是在拿自己的一辈子开玩笑!”母亲哭了。
但我还是坚持。
订婚宴那天,来了很多村里人。
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像在看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人。
陈默的舅舅是村里的老毕摩,他对我笑了笑,但那笑容让我浑身发冷。
“新娘子,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什么?”
“净化仪式。”他的声音低沉,“新婚夜的净化仪式。”
“那是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说,“需要褪去旧的,才能迎接新的。”
饭后,陈默的母亲带我去看婚房。
推开门,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墙上贴满了神像,中央摆着巨大的铜制火盆,旁边有七个蒲团。
角落里有个黑色木盒,我打开一看,里面是把银刀,还有装着黑色液体的瓶子。
整个房间弥漫着刺鼻的药香。
“这些是干什么用的?”我问。
“仪式要用的。”陈默的母亲说完就走了。
我看着那些东西,突然很想逃离。
但想起陈默的眼神,想起他说“如果你走了,我就真的没救了”,我咬了咬牙。
婚礼当天,天气很好。
陈默穿着红色婚服,但里面还套着好几层衣服。
拜堂时,他突然脸色煞白,额头冒冷汗。
老毕摩端来一碗黑色汤药:“喝了。”
陈默接过碗,手抖得厉害。
他闭着眼睛喝完,脸色更加苍白。
“这是什么?”我问。
“压制疼痛的。”老毕摩说。
林月突然从人群里冲出来,抓着我的手臂哭喊:“苏晚姐!现在走还来得及!”
七八个人把她强行拉开。
她还在拼命喊:“你会后悔的!你会疯的!”
老毕摩走到我面前:“新娘子,如果受不了,可以喊停。”
他指了指陈默:“但喊停了,他这辈子就毁了。”
陈默看着我,眼眶通红。
他握住我的手:“苏晚,对不起。”
我深吸一口气:“走吧。”
05
现在我就站在这个房间里。
七个毕摩围坐在火盆边,诵经声低沉诡异。
陈默被蒙着双眼,坐在中央的蒲团上。
他的身体在剧烈颤抖,尽管他努力控制着。
两个老阿妈的手搭在他白袍的肩膀上。
白袍的扣子被一颗一颗解开。
第一颗。
第二颗。
第三颗。
我的心跳快得要炸开,耳朵里全是自己的心跳声。
我忽然想起母亲寄来的护身符,就在我的口袋里。
林月扔给我的铜镜,也在我袖子里。
白袍从肩膀开始滑落。
我的手伸进口袋,握住了那个发烫的护身符。
铜镜从袖口滑出,“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白袍继续滑落。
我终于看见了。
我双膝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