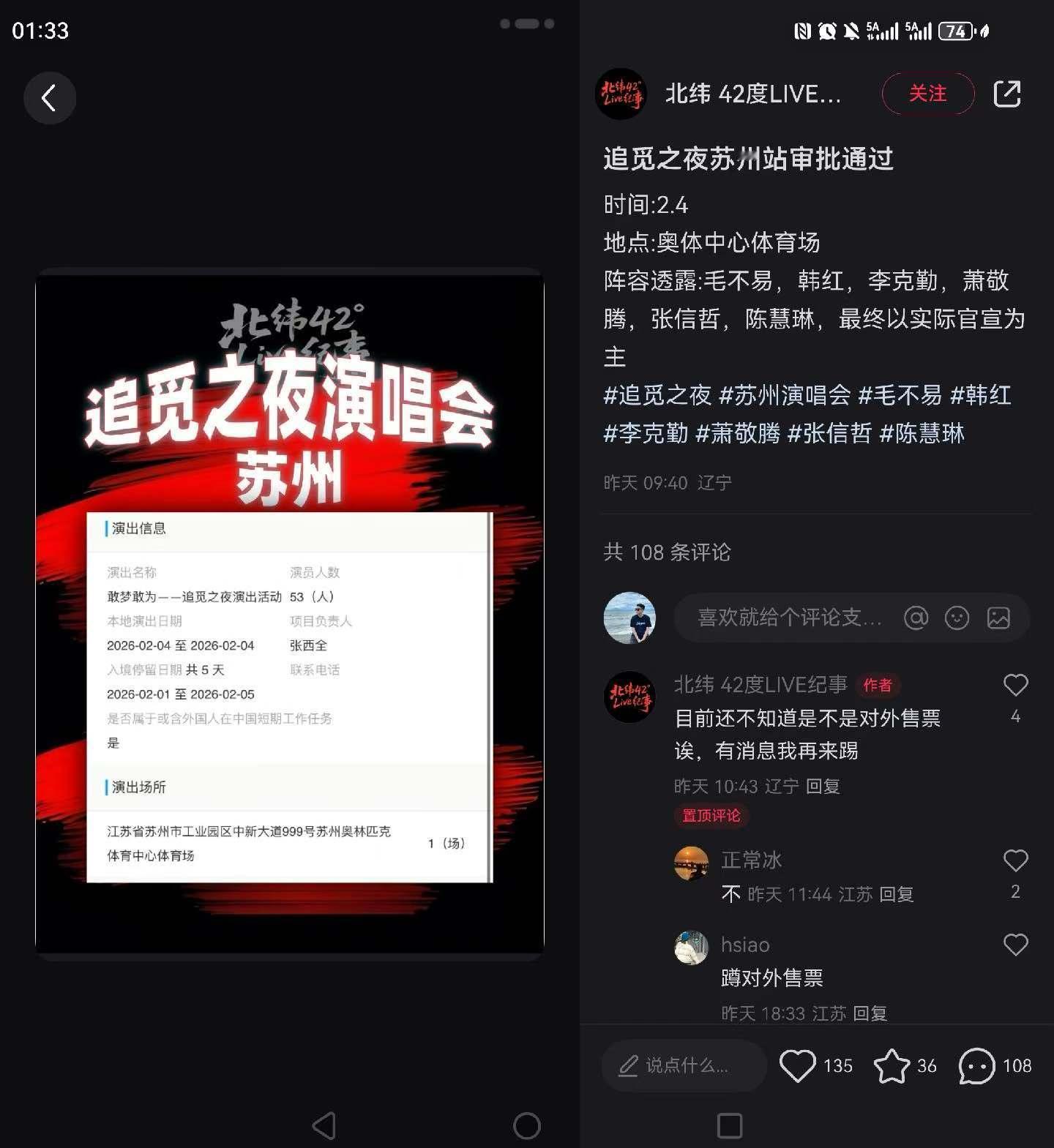文/幸福娃

冬夜读书,偶见两句旧诗:“只因错赏昔日雪,一夜悲萧到天明。”心里像被什么细锐的东西轻轻刺了一下,不很疼,但那凉意却缓缓地漫开。
放下书,窗外正黑沉沉的,看不见雪,却仿佛能听见那穿过漫长夜色的、呜咽似的箫声。
这大约是人心里一种极寻常,又极磨人的境况吧:走不出的,常常不是当下的泥淖,而是昨日一片澄澈的、已化的雪。
我们大约都有过“错赏”的时候。那“昔日雪”,美是顶美的,纷纷扬扬,下在记忆的山谷里,将芜杂的、不堪的都覆得一片纯然皎洁。
人站在时光的这一头回望,眼里便只剩下那一片无瑕的白,忘了当时彻骨的寒,忘了行路的蹒跚,甚至忘了自己为何走到那片雪地里去。
那雪,或许是少年时一段无果的情愫,或许是人生路口一个未竟的选择,又或许,仅仅是一种早已消逝的、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心境。
我们总爱回头去赏它,一遍又一遍,像抚摸一块温润的旧玉,用如今的体温去焐热它,也焐热那个立在雪中的、年轻的自己。
错的是那赏的“姿态”,我们赏的,往往不再是那场真实的雪,而是我们亲手用怀念的云雾织就的幻影。
时光是一架奇妙的筛子,它漏去了琐碎、烦恼与苦涩,独留下些晶亮的、看似纯粹的片段。
我们将这零落的片段拾起,精心缀成一幅完满的图景,挂在自己心室的墙壁上,日日相对。
错就错在,我们将这心造的幻影,当作了可以归去的故园;将那一瞬的雪光,当作了可以取暖的永恒炉火。
我们吹着箫,吹的是对幻影的迷恋,也是对这般沉迷的自己的几分怜惜与埋怨。
那箫声,呜呜咽咽,不成曲调,因为它本就不是吹给旁人听的,它是自己与自己漫长的、絮絮的交谈。
谈往昔,谈如果,谈失落,谈那无论如何也追不回的“当时”。
一夜又一夜,仿佛要吹到那昔日的雪重新落下才肯罢休,却不知,天明时分,晒干泪痕的,终究是今日的太阳。
这便像走进了一条没有出路的回廊,我们在里面踱步,四壁挂满了昔日雪景的画卷,我们看得痴了,忘了去寻那通向当下园子的门。
沉湎于过去的好,与沉湎于过去的坏,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将生命的力,虚耗在了一幅已经封笔的画上。
你对着它赞叹,对着它流泪,对着它扼腕,它自岿然不动,你却已筋疲力尽。
那箫声,吹得愈久,心便愈空,像一间摆满了旧家具却无人居住的屋子,只有穿堂风寂寞地游荡。
窗外此刻,或许是春日的泥泞,或许是夏夜的虫鸣,那才是你真切活着的人间。
那场雪,就让它安然地活在“昔日”的位置上,像一页夹在旧书里的干花,你可以记得它的模样,却不必再祈求它重焕生机。
这清醒,说来容易,却要经历无数次“悲箫到天明”的夜晚才能换来。
那箫声,未必全是坏事。它像是灵魂在沉闷中自寻的出气孔,是郁结的情绪自己找到的、曲折的流淌。
只是,我们不可任凭这箫声没完没了地吹下去。要在那悲凉的调子里,渐渐听出一点对自己的告诫,一点对明天的眺望。
要晓得,那吹箫的人,与那赏雪的人,原是自己;而这决定放下箫管,推开窗户,迎进今日第一缕晨光的人,也依然是自己。
杨绛先生曾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这淡定与从容,我想,绝不是对“昔日雪”视而不见的健忘,而是能平静地收纳它,承认它的美与它的逝去,而后,转过身来,好好打量眼前这个或许并不完美、却真实无比的此刻。
我们的生命,终究是一条不能倒流的河。上游的雪水固然清冽,但滋养我们此刻的,是中游与下游那更为浑厚、也更富含养分的水流。
窗外的夜色,似乎淡了一些。想象中的箫声,不知何时也止息了。屋里静悄悄的,只有暖气片发出极轻微的嗡鸣。
我们每个人心里,或都藏着一场“昔日雪”,也都有一管吹给它的“悲箫”。 只是莫要让那箫声,占尽了所有的夜晚。
天,总是要亮的,而天亮之后,我们要去照看的,是窗台上那盆真实的、需要浇水的绿植,是书桌上那本才翻到一半的、属于今天的书。
昨夜那场关于雪的梦,让它淡淡地散去吧,如晨雾一般。毕竟,我们赶路的人,身上沾的,应是这一路的尘与露,而非早已化尽的、昨日的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