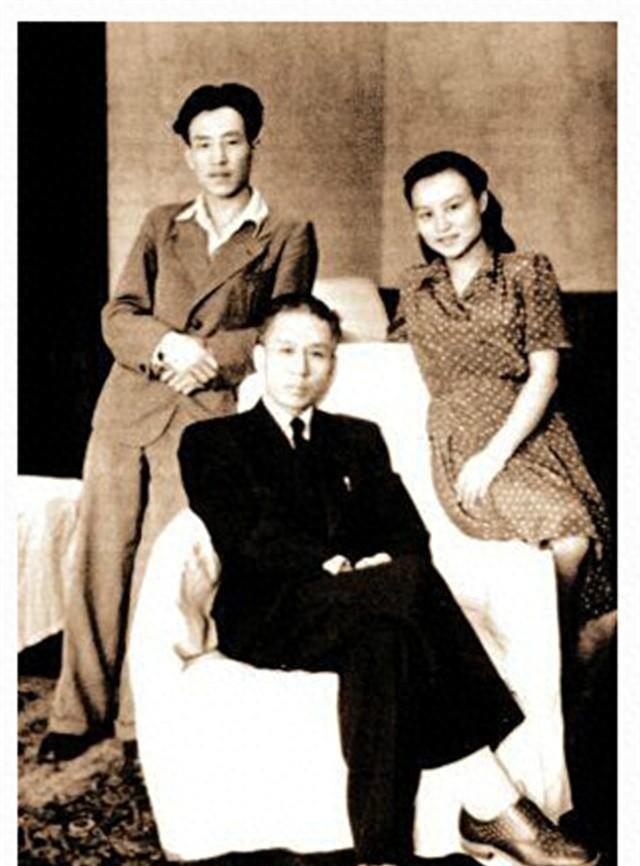1972年,知青张援朝去看望干妹妹陈春玲,谁知,陈春玲红着脸说:“我这病,你娶我就好了!”张援朝父亲听说后,板着脸说:“娶了她,你还能返城吗!” 陕北孙家沟的土窑洞里,陈春玲正蜷缩在打满补丁的被子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走了十几里山路的张援朝从北京知青点赶来,走到炕边,俯下身,询问她的病情。 陈春玲艰难地睁开眼,突然她哭着说:“援朝哥,我这病怕是治不好了,除非你娶了我,兴许就好了。” 话音未落,又是一阵咳嗽。 1969年,一列绿皮火车,将17岁的北京四中学生张援朝送到了这片黄土地上。 他和几十名知青一起,被分配到延川县孙家沟插队落户。 城市少年初到农村,日复一日的繁重农活,让他感到无所适从。 就在这时,陈春玲走进了他的生活。 她是生产队记分员陈老汉的女儿,那年刚满16岁,梳着两条乌黑油亮的麻花辫。 她性格泼辣爽朗,是村里有名的“铁姑娘”。 面对这群来自大城市、笨手笨脚的学生娃,她没有嘲笑,而是像对待自家兄弟一样,耐心地帮他们适应陕北艰苦的生活。 张援朝永远记得,当他第一次笨拙地弄锄头差点伤到自己时,是陈春玲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 作为回报,张援朝承担起教陈春玲识字的任务。 村里条件简陋,夜晚,在窑洞里一盏煤油灯下,张援朝用树枝在泥地上写下“人”、“口”、“手”,陈春玲学得极其认真。 张援朝发现,这个看似大大咧咧的农村姑娘,内心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 张援朝被她的坚韧和聪慧深深打动。 在黄土高原上,两颗年轻的心在共同劳动和学习的朝夕相处中,悄然靠近。 张援朝的父母得知儿子在陕北认了个“干妹妹”,还特意寄来糖果和布料表示心意。 陈老汉一家也真心实意地把这个有文化的北京娃当成了自家人,家里做了点好吃的,总要给他留一份。 张援朝在陈家的窑洞里,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猝不及防。 1972年,一场罕见的寒流席卷陕北,陈春玲在参加公社兴修水利的“大会战”中,顶着刺骨寒风在冰水里劳作数日,不幸染上重病。 起初是持续的低烧和咳嗽,村医诊断为普通风寒,开了些草药。 但病情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日益沉重。 咳嗽越来越厉害,有时甚至咳出血丝,人也迅速消瘦下去,整日无力地躺在炕上。 那个曾经像充满活力的“铁姑娘”,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 张援朝心急如焚,他深知村里的赤脚医生能力有限,也清楚当时整个延安地区医疗资源的匮乏。 他多次向生产队和公社反映,希望能送陈春玲去县医院治疗,但得到的答复总是“条件有限”。 看着干妹妹日渐憔悴,张援朝心如刀绞。 他省下自己微薄的口粮和津贴,托人从县城买来稍好一点的药,但效果甚微。 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当他再次踏入陈家窑洞,听到那石破天惊的“治病”请求时。 他明白,这并非真的相信“冲喜治病”的愚昧,而是一个深陷病痛的少女,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中,向她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发出的求救信号! 张援朝僵立在炕边,手腕被陈春玲的手死死攥住。 娶她?他并非对她无情。 然而,他是北京知青,他的根在千里之外的城市。 就在不久前,队里干部还暗示他,因为他有文化、表现好,是“好苗子”,未来可能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远在北京的父母,对他寄予厚望。 父亲是严谨的知识分子,母亲是中学教师,他们绝不会接受儿子娶一个陕北农村姑娘,一个身患重病、前途未卜的农家女! 一旦结婚,他就可能与返城的机会彻底绝缘! 几个月后,1973年春,张援朝因在插队期间表现突出,被生产队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生选拔,并成功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 消息传来,孙家沟沸腾了。 当录取通知书送到张援朝手中时,他百感交集。 临行前,他鼓起勇气再次来到陈家。 陈春玲的病情在村医的草药和时间的流逝中,竟奇迹般地有所好转。 她没有哭闹,没有指责,甚至没有提那天的事。 时光荏苒,张援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安工作,后调回北京,在城市规划研究所任职。 他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过上了标准的城市知识分子生活。 然而,夜深人静时,总会总会想起当年的生活。 他与陈春玲保持着断断续续的书信联系,知道她后来嫁给了同村一个憨厚的后生,生了三个孩子,成了一个普通的农妇。 1978年,知青大规模返城。 民政部后来的调查显示,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婚姻,有72.3%以离婚告终。 张援朝有时会想,如果当年他选择了留下,结局又会如何? 2015年春天,一封来自陕北的讣告寄到了北京。 陈春玲的儿子在信中说,母亲因病去世,临终前只是偶尔会翻看一张老照片。 张援朝重返阔别四十多年的孙家沟。 陈春玲的小儿子递给他一张保存完好的单人照,正是当年他给她拍下的、在土墙前写字的侧影。 主要信源:(《中国知青下乡运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