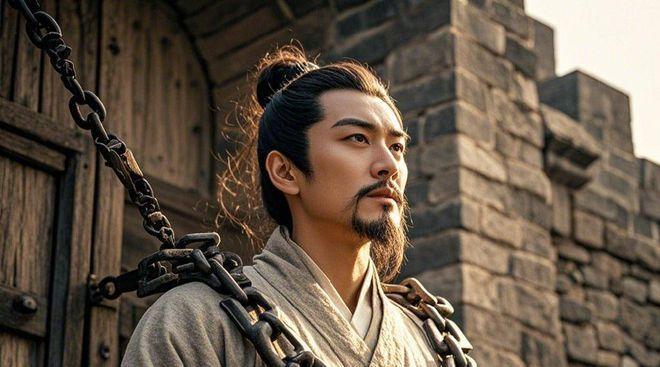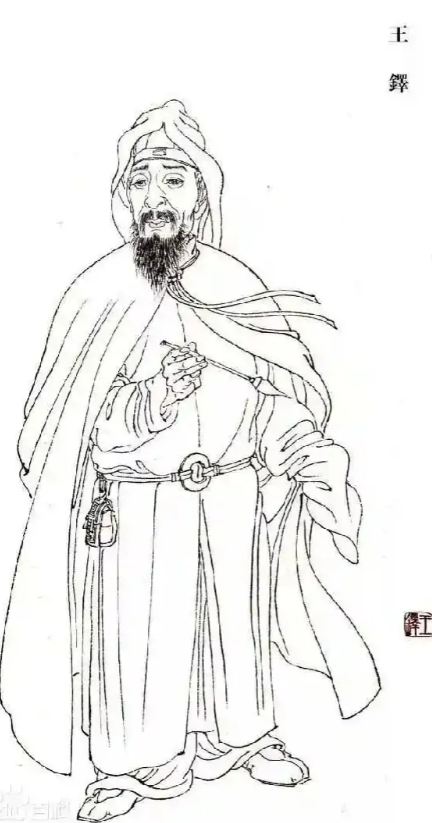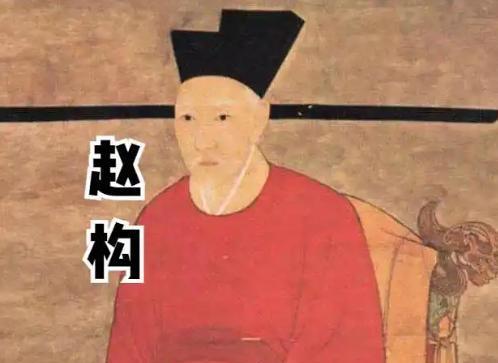刑场之外,雪尚未化,风割脸如刀。一个女人跌跌撞撞奔至,跪倒尸前。她伸手翻开襟口,一纸字迹映入眼帘。瞬间,她泪如雨落,面如死灰。元帝口中的“慈悲”,成了她无法承受的审判。她伏在尸身上,低语无声。半晌后,一动不动。 江西庐陵,江水绕村。文家得子,取名天祥,字履善,自号浮休道人。他自小聪慧,十岁能诗,十五通经。父亲早逝,母亲严教。他寒窗苦读,弱冠之年,踏上进京之路。 1256年,宝祐四年,他高中状元,成为万众敬仰的新星。起初任官江西提刑,再升礼部侍郎,后入枢密,终至右丞相。他心怀家国,一身正气,不近权贵,不避锋芒。 元军南下,朝局动荡。皇族南逃,主战主和分裂。他力主抗元,上疏陈策,不惜与主和派激烈争执。被贬、复起,几经沉浮,他始终站在抵抗最前线。 1278年,海丰失守,文天祥被俘。他曾两度自刎,一次绝食,皆未死。他不求生,只求不辱。他被押北上,铁索加身,风雪兼程。他知道前路无归,但他不肯低头。 大都之行,是他最后的归程。他边走边写,《正气歌》《指南录》一篇篇落笔。他不怕死,他怕死得不明。他写给后人,也写给自己。 元帝忽必烈听闻文天祥,既忌其名,又惜其才。多次劝降,承诺高官厚禄。文天祥听了,只一笑置之。他话不多,但眼神像刀。他的脊梁笔直,从未弯下。 他被关押在大都的牢房。白日写字,夜晚吟诗。他不求翻案,不求宽赦。他只求死得像个南宋人。 三年囚禁,寒暑交替。有人劝他“苟且偷生”,有人替他请命。他都不动。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他写的,也是他活的。 大都百姓敬他。即使是敌国之地,仍有人暗中送饭、赠纸笔。他不领情。他写《过零丁洋》时,已将生死放下。他的忠,不是做给谁看。他的死,是对朝代的交代。 忽必烈终失耐。1283年十二月初九,命令执行死刑。 柴市,刑场,雪未融。文天祥行至刑前,仍向南跪拜。他望着南宋故都方向,三叩首后,从容就义。 刀落,无声。人群静默。他死了,但不是输。 文天祥死后,元廷下诏,允其妻欧阳氏收尸。 这并不是恩典。她早被贬为官奴,在宫中杂役,身份低贱,地位卑微。忽必烈这一手,不过是做个“宽仁”姿态。可对欧阳氏而言,却是劫后余痛。 她闻讯奔出,风雪中徒步赶往刑场。她穿着破布奴衣,脚无鞋袜,步步踉跄。 抵达时,尸体尚温,血未干。她跪在丈夫身旁,颤手解开他外袍襟口。忽见布内有纸。抽出细看,字迹清楚,是丈夫留给她的绝笔: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这句话,她太熟了。他曾无数次吟诵。如今写在衣中,是写给天下,也是写给她。 她沉默许久,泪水无声滴落。她知道自己苟活至今,是屈辱。他死得从容,而她……羞愧难当。 人群中无人劝她。她只是静静伏在尸体上。然后,悄无声息地,自尽。 有人说她用发簪抹喉,有人说她撞墙而亡,无从查考。但可知,她死得安静。她终于,追上了他。 文天祥死后,尸体被妥善收殓,葬于北京南郊。他的诗、文、骨气,被后人代代传颂。 欧阳氏的事迹少有人提。但历史记得她。她不是烈女,也不是忠贞典范。她曾为奴,曾苟活。可在那一刻,她没有逃避。她明白了他的坚持,明白了自己的沉默。 她以死谢他,也以死洗清自己的耻辱。 南宋灭亡多年,江山换姓。可文天祥的《正气歌》,却成了后人心中的灯。 他死时47岁,一生几经沉浮,却始终不改其志。他用笔,用血,用命,证明一个读书人的底线。 欧阳氏陪他走完最后一程。他们未曾在生同堂,却能共赴死境。那纸绝笔,刺痛她,也成全了她。 有些死,是光荣。有些死,是救赎。他们的死,是两者兼具。 柴市刑场,已无踪迹。可每当寒风乍起,人们仍会记起那个场景: 一个男人跪拜南方,一个女人伏地而亡。 风中,依稀有人轻声诵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