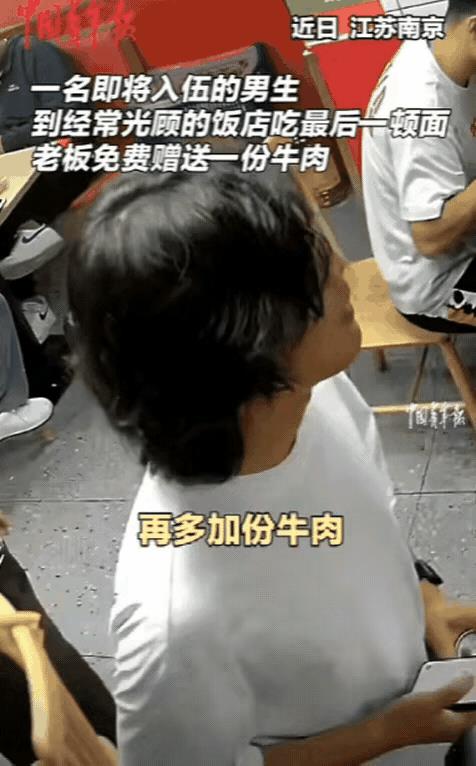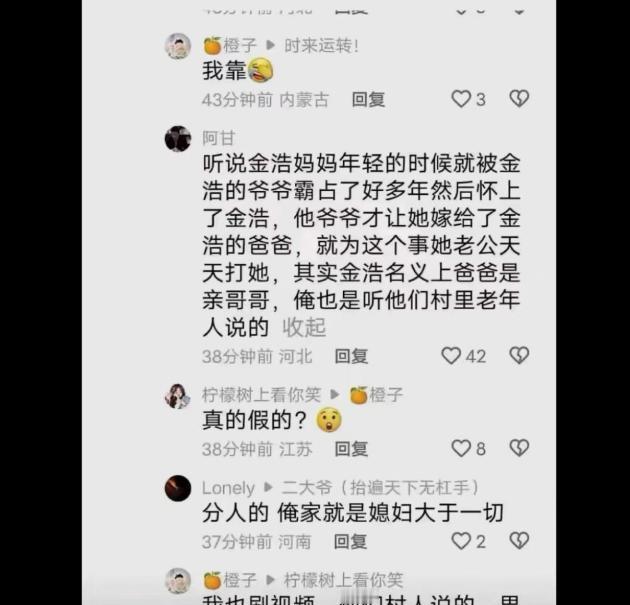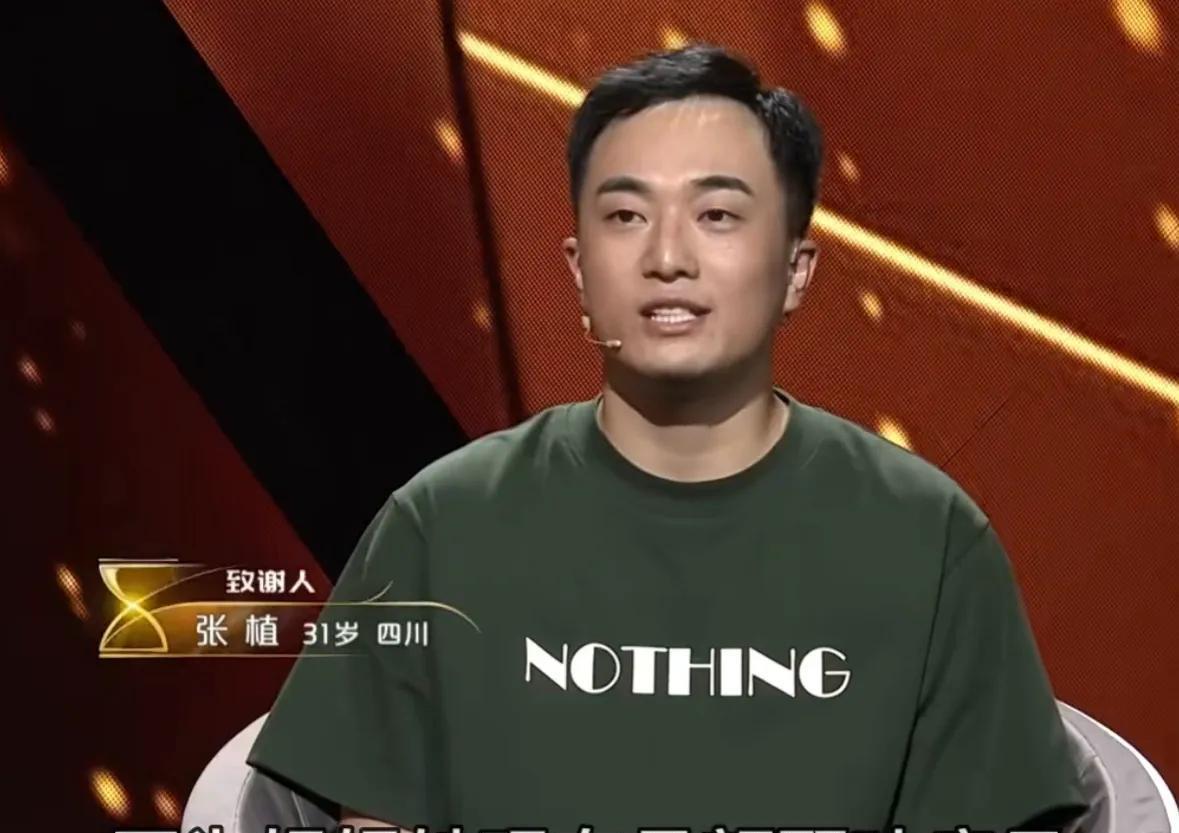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她是什么人?哪来的这么多钱?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4年的北京,秋天刚到,风里带着点凉意,一个穿着旧棉袄、脚蹬布鞋的老太太走进了政府接待处,手上的布包已经磨得起毛,拐杖也是用旧木头削的,她一身灰扑扑,看起来像是刚从胡同里扫完地出来,谁也没想到,她是来捐款的,而且是24亿。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在那个年月,一户人家月收入几十元,家里能攒下几千块钱都算富裕了,可这个老太太,站在那里说要把几十亿上交国家,工作人员一时都以为她糊涂了,可她不是糊涂,她特别清醒。 她叫耿维馥,在北京西城区的几个胡同里提起她,认识的人都说她脾气好,说话轻声细语,干活从不偷懒,几十年如一日扫街,从不迟到早退,她吃得简单,穿得朴素,攒下的工资不是给孩子买新衣服,而是捐给孤儿院、灾区、福利所,很多人以为她只是个太节俭的老人,其实她是个藏着大秘密的人。 年轻时的耿维馥生活在沈阳,那时候她是耿家大小姐,家里做布匹生意,殷实富足,她聪明好学,却偏偏在一次讲座里看上了演讲台上的赵欣伯,这个男人长相周正,穿着西装,说话带着点洋气,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正意气风发,耿维馥一心一意喜欢上了他,不顾家人劝阻就嫁了过去。 这场婚姻并不顺利,赵欣伯原来有过妻子,名字叫碧琰,成亲后,他竟然让耿维馥改名为赵碧琰,耿维馥虽然心里不好受,但还是照做了,她以为忍一忍,日子会好转,可没想到,赵欣伯的仕途越走越偏,最后竟然投靠了日本人,成了伪满洲国的官员。 那段时间,赵欣伯通过职务之便捞了不少钱,还在日本置办了不少房产,但他怕这些财产日后会被追查,就全登记在妻子名下,耿维馥并不知情,她只知道丈夫越来越冷漠,越来越不像当初那个人,她试着劝他,换来的却是冷言冷语和一次次失望。 1945年,日本战败,赵欣伯被押回国内,因为汉奸罪名,他被关进监狱,不久后就死在牢里,耿维馥带着孩子回到北京,改回原名,开始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她不再是耿家小姐,也不是谁的太太,而是一个靠扫地糊口的普通人。 她从来不提过去的事,别人问她为何吃得这么省,她只说“习惯了”,有人说她年纪大了不该干体力活,她只是笑笑,不多解释,每天早上,她推着扫帚穿过胡同,打扫街道上的落叶和尘土,回家后,烧一锅玉米面粥,再分出几块钱悄悄塞进捐款箱。 没人知道她每年清明都要去一次万安公墓,在无名烈士碑前放一束白菊,她从不带人去,也不说原因,她做这些事,不为表扬,也不为感动别人,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 几十年过去,北京变了样,胡同也越来越少,耿维馥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得更厉害了,她的孩子们都成了家,各自过着平淡的日子,她从不向他们提起赵欣伯,更不谈当初的财产。 直到1984年,有关部门找上门来,说她可能是日本一笔巨额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原来,赵欣伯在日本留下的地产和资金,在战后几十年间升值巨大,总额超过三十亿日元,因为财产登记在赵碧琰名下,日本方面迟迟无法处理,而耿维馥,是唯一的合法持有人。 政府派人协助她出示证据,提交结婚证明、出生记录、存档资料,那些她保留了一辈子的旧文件,终于派上了用场,官司打了二十年,期间有两百多人冒充赵碧琰,企图分一杯羹,但最终,她赢了。 拿到存单那天,她已经84岁,眼睛花了,手也不稳,她看着那串零,沉默了许久,然后做了一个决定:把其中的24亿捐给国家。 她没有犹豫,不是为了名声,也不是想搏谁一句“高尚”,她只是觉得,这笔钱是赵欣伯当年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如今就该还回去,她自己过的已经够久,这笔钱,她用不上;她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不该靠这些钱活着。 她把捐款用途写得清清楚楚:一部分用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一部分用于修建偏远地区的学校,剩下的作为抗灾备用,她不求回报,只希望这些钱,真的能帮到需要的人。 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很多人震惊于她的选择,也有人不理解,但她没有接受采访,也没有出席任何表彰,她照旧扫她的胡同,穿她的旧棉袄,推车、扫帚、饭盒一样不少。 1990年,她在北京的老宅里去世,去世时没有遗言,只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几句话:“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账,我已经结了,” 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她枕下压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1921年的沈阳,一座教堂前,站着一对新人,男人穿着西装,眼神清澈;女人笑得腼腆,握着他的手。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汉奸丈夫”在日本留下巨额遗产,她花21年追讨成功,捐给国家24亿

![目前拍的最有感觉和科技感的东大地装图[爱心][爱心][爱心]](http://image.uczzd.cn/17788273067535969915.jpg?id=0)

![刚刚刷到一个新闻一个男子每天花180块钱[惊恐]用6个小时,从河北坐高铁赶](http://image.uczzd.cn/616324198791966655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