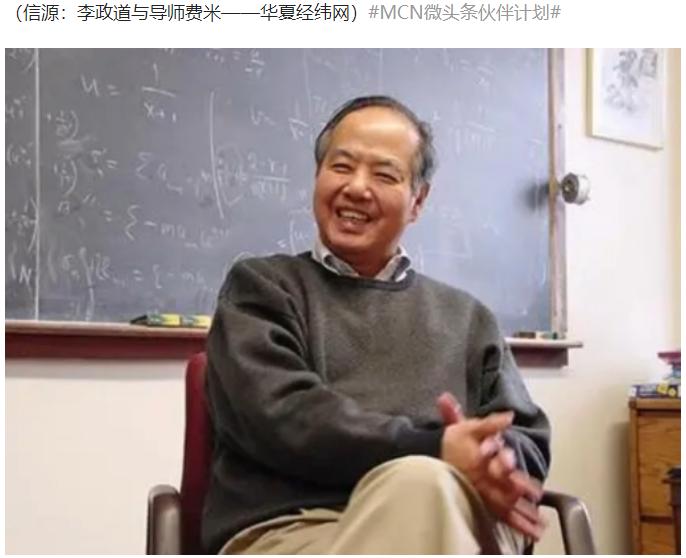1946年,老师突然问到:“太阳中心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脱口而道:“我从书上看过,大概1000万度。”费米听完批评他:“你这样是不行的!” 彼时21岁的李政道刚从西南联大赴美,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还带着学生对书本知识的依赖,却没料到这句批评会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启蒙警钟”。 费米从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而是每周留出固定时间,把李政道叫到办公室,从太阳温度的计算模型聊起,追问他“这个数值是基于哪个实验数据”“如果改变恒星密度假设,结果会怎么变”。 有次两人为验证主序星内部能量传输理论,费米甚至带着李政道一起手工制作计算尺,从刻度校准到公式推导,每一步都要求“不仅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这种近乎“较真”的治学态度,慢慢刻进了李政道的骨子里——后来他在研究中,哪怕面对再权威的理论,都会先回头核查原始实验数据,这份严谨,正是源自费米当年的言传身教。 在费米门下的三年,李政道的学术潜力彻底被激发。1949年他拿到博士学位时,已在《物理评论》发表多篇关于量子场论的论文,其中一篇对“核子散射振幅”的计算,还被费米在课堂上当作案例讲解。 那时费米常对人说:“李政道身上有种特别的劲头,他不满足于‘记住答案’,总想着‘推翻答案再重建’。” 这种劲头让他后来与杨振宁的合作水到渠成——1956年,两人针对“θ-τ介子衰变矛盾”,大胆质疑物理学界公认的“宇称守恒”定律,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猜想。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他们反复核对了过去30年的所有相关实验报告,发现竟没有一项实验能真正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 随后吴健雄团队用钴60实验证实了他们的理论,这一发现直接改写了粒子物理的基础框架,也让31岁的李政道在1957年成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史上最年轻的得主之一。 站在领奖台上时,他特意提到费米:“如果没有他教会我‘追问根源’,我或许永远不会有勇气挑战权威。” 2024年11月的苏州,东山镇华侨公墓里多了一座合葬墓,97岁的李政道终于回到祖籍,和去世多年的夫人秦惠䇹团聚。 这位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老人,走时惊动了中外物理学界,归时却带着一身烟火气,就像他这一生,既攀过科学的珠峰,也始终踩着祖国的泥土。这份对故土的牵挂,从他成名后就从未断过。 1972年,中美关系刚缓和,李政道就顶着压力回国访问,成为改革开放前少数能往返中美之间的科学家。 他第一次回到北京时,特意去了北大物理系,看到学生们因缺乏前沿资料只能啃旧教材,当场就承诺“要帮祖国打通学术交流的通道”。 1979年,他牵头创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亲自设计考试大纲、筛选招生院校,甚至利用自己的人脉说服美国20多所顶尖大学参与。 短短10年,这个项目就选拔出915名中国学生赴美深造,如今这些人里出了6位中科院院士、3位美国科学院院士,还有人成为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物理系的领军人物,撑起了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半壁江山”。 李政道为祖国做的远不止这些。他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奖金、常年讲学的收入攒起来,在1994年以夫人秦惠䇹的名义设立“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专门资助国内本科生进入科研实验室实习。 截至2023年,已有近万名学生通过这个基金接触到前沿科研,其中不少人后来投身于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等“卡脖子”领域的研究。 他还多次回国举办学术讲座,哪怕到了80多岁,仍坚持站在讲台上,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学生讲粒子物理,有次讲完课被学生围住提问,他耐心解答了两个多小时,临走时还叮嘱“有问题随时给我发邮件”。 身边人劝他少劳累,他却说:“我当年能有机会跟着费米学习,是运气;现在能帮祖国的年轻人多走一步,是责任。” 晚年的李政道,依然保持着对科学的热情和对祖国的惦念。90岁时,他还在修改关于暗物质探测的论文,逐行核对卫星观测数据,助手劝他“简化一些推导过程”,他却摇头:“费米当年教我,科学里没有‘差不多’,数据差一点,结论可能就差十万八千里。” 同时,他开始整理自己的学术手稿和书信,捐给上海交通大学的“李政道图书馆”,希望这些资料能给后辈留下参考。 他常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苏州东山,不管走多远,最终都要回来。”如今,他与夫人合葬在故乡的土地上,墓碑上没有堆砌任何头衔,只刻着两人的名字和生卒年份,就像他这一生——在科学领域光芒万丈,却始终以最朴素的姿态,守护着对学术的敬畏和对祖国的深情。 从费米门下那个被批评的年轻学生,到成为祖国物理学界的“摆渡人”,李政道用一辈子的时间,诠释了什么是“既要攀科学高峰,也要守故土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