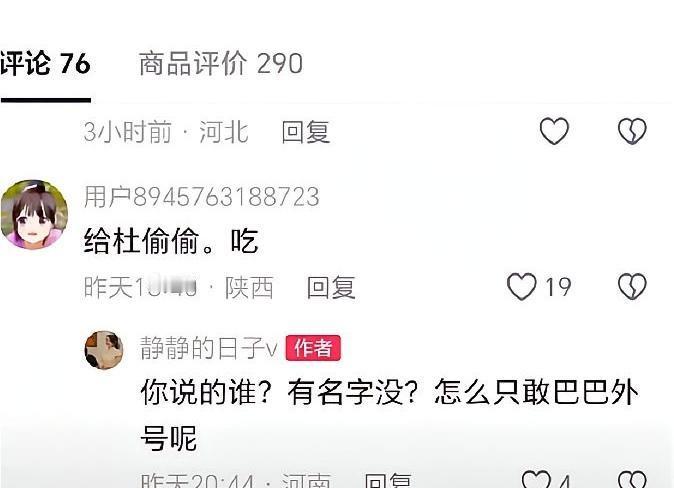我三叔的鱼塘被人投了药,一池子鱼全翻了肚皮。 三叔蹲在塘边抽完半包烟,起身去镇上买了把斧子,斧刃有巴掌宽。 他回村没直接找仇家,先去了祠堂,把斧子哐当扔在供桌上。 管祠堂的老太公正在擦牌位,手一抖,布掉在地上。 三叔说,老太公你知道我为啥来,我鱼塘的事全村都清楚。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这事村里管不管? 要是不管,我就在这儿等到晌午,晌午过后我自己管。 老太公颤巍巍摸出手机,说马上叫村长来。 三叔拉把椅子坐下,盯着供桌上的斧头,说行,我等到十二点。 祠堂里飘着陈年的香灰味,供桌前的香炉里插着三支没烧完的香,烟慢悠悠往房梁上缠。 三叔的手指在膝盖上敲,节奏跟他蹲塘边抽烟时一个样,一下,又一下,像是在数翻肚皮的鱼。 村长骑着电动车赶来时,车筐里的铁饭盒哐当响,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褂子领口全湿了,贴在背上像块黑膏药。 “老三,你先把斧子收起来,有话咱慢慢说。”村长伸手想去碰斧子,被三叔一个眼神顶了回去。 老太公拿拐杖敲了敲地:“都别吵吵,先去塘边看看,药瓶子还在不在?” 一群人呼呼啦啦往鱼塘走,三叔走在最后,斧子扛在肩上,斧刃蹭着他后脖颈,凉飕飕的。 塘边的泥地上果然有个碎药瓶,标签撕了一半,剩下的边角印着个红太阳图案——镇上供销社卖的那种玉米杀虫剂,村里好几家都用过。 “谁家用这种药?”村长蹲下来捏了捏碎玻璃,“瓶底有新鲜的鞋印,38码,像是双解放鞋。” 人群里有人嘀咕:“老刘家二小子前几天跟三叔吵过架,说鱼塘挡了他家地的采光……” 三叔没说话,眼睛扫过围观的人,突然往塘埂另一头走——那里有丛芦苇,芦苇底下压着片蓝布,露出半截带子,看着眼熟。 他拨开芦苇,把蓝布扯出来,是件小孩的褂子,胸前绣着只歪歪扭扭的小狗,袖口还沾着点黄色药粉,跟药瓶里的一个色。 这褂子咋看着这么眼熟? 三叔心里咯噔一下,想起前天去村东头老马家串门,见老马的孙子穿着件一模一样的,那孩子才六岁,说话还漏风。 他转身就往老马家跑,斧子在肩上颠得哐哐响,路过晒谷场时,惊飞了一群麻雀。 老马正在院里编筐,见三叔扛着斧子冲进来,手里的柳条啪嗒掉在地上:“老三,你这是干啥?我家娃招惹你了?” 里屋的门帘一挑,小马驹举着个空药瓶跑出来,嘴里还喊:“爷爷,药,鱼鱼……” 那药瓶跟塘边的碎瓶子一个样,瓶盖上的红太阳图案缺了个角。 “你给我站住!”老马一把抓住娃,脸都白了,“你拿药瓶干啥去了?” 小马驹被吓得直哭:“我,我去喂鱼,瓶瓶上有鱼……”他小手比划着,“倒,倒进去,鱼鱼就睡觉了……” 三叔盯着娃沾着泥的裤脚,那泥里混着几根芦苇絮,跟塘埂上的芦苇一个样。 原来不是仇家,是老马的孙子偷拿了药瓶,以为瓶上的图案是鱼食,偷偷倒鱼塘里了。 三叔蹲下来,把斧子放在地上,摸了摸小马驹的头,那孩子还在哭,鼻涕蹭了他一胳膊。 他想起去年收玉米,老马帮他扛了两袋,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想起开春他鱼塘放水,老马挑着担子来送水,说怕他渴着。 村里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为地界红过脸,为引水渠吵过嘴,可谁家真有过不去的坎,半夜敲门借袋米,也没见谁关过门。 “娃不懂事,不怪他。”三叔站起来,把斧子往肩上一扛,“药钱我自己出,你以后把药放高点,别让娃摸着。” 老马嘴唇哆嗦着,要给三叔磕头,被他一把拉住:“磕啥头,我还等着吃你家娃的满月酒呢。” 三叔回祠堂时,老太公还在擦牌位,供桌上的斧子不见了,换成了个粗瓷碗,里面盛着刚沏的茶,茶叶在水里打着转。 “斧子我让村长收库房了,”老太公说,“留着冬天劈柴,比扔这儿吓唬人强。” 三叔端起茶喝了一口,烫得他龇牙咧嘴,可心里那股火,像是被这热茶浇灭了,剩下点余温,暖烘烘的。 后来小马驹见了三叔,总躲在老马身后,探出半个头喊“三叔”,手里还攥着颗糖,非要塞给他。 三叔的鱼塘又放了新鱼苗,这次他在塘边围了圈篱笆,上面挂了个木牌,写着“娃莫靠近,有虫药”,字歪歪扭扭的,跟小马驹绣的小狗一个样。 遇到事别急着攥拳头,先看看是不是有个小娃举着药瓶,以为在喂鱼——人心不是铁打的,有时候弯下腰,比扛着斧子更有力量。
![胖东来的工资充分,尊重了劳动人民[鼓掌]](http://image.uczzd.cn/532247166302472564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