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1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刚到英国三天,时差都还没倒过来,就和人发生了关系,连基本的防护措施都没做。一周后查出性病,对方轻飘飘一句“just for fun”——就是玩玩而已。姑娘当场就懵了,后来她让那个男的去做检查,换来的不是道歉或解释,而是几刀子。男的被捕后还说自己是自卫,“只是想让她离远一点”。 2024年3月的伦敦,初春的冷雨裹着寒意,敲打着刘易舍姆区那栋红砖公寓的玻璃窗。王喆拖着还没倒过来时差的身体,把最后一个行李箱塞进房间角落。墙上的电子钟显示当地时间凌晨三点,国内已是上午十一点——她三天前才踏上这片土地,行李箱里还装着母亲塞的晕车药,和一张写满注意事项的纸条。 作为31岁的研究生新生,王喆对英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出发前做的攻略里:古老的城堡、飘着咖啡香的街道、图书馆里安静翻书的身影。抵达当晚,她在学生公寓的公共厨房遇到了一个叫汤姆的本地男生,对方笑着帮她拧开顽固的罐头,蓝色的眼睛里盛着礼貌的热情。“欢迎来到伦敦,”汤姆递过一杯热可可,“这里的夜晚比白天更有趣。” 王喆的心弦被轻轻拨动了。独自在异国的孤独、学业压力带来的焦虑,让她对这份突如其来的热情卸下了防备。三天后的晚上,汤姆约她去公寓附近的酒吧,昏暗的灯光下,他讲着荒诞的笑话,酒杯碰撞的声音里,王喆渐渐喝多了。离开时,汤姆顺理成章地牵起她的手,她没有挣脱。 回到汤姆的住处,墙上的挂钟指向午夜。酒精模糊了理智,王喆忘了母亲“在外要保护好自己”的叮嘱,也没想起出发前疾控中心朋友塞的防护用品。当汤姆靠近时,她闭上眼,只觉得窗外的雨好像停了,空气里有种不真实的暖。 一周后,王喆的身体开始不对劲。私密处的瘙痒让她坐立难安,去社区医院检查时,医生递来的化验单上,“衣原体感染”几个字像冰锥刺进眼里。她攥着化验单的手在发抖,第一个念头就是找到汤姆。 电话接通时,汤姆的声音带着宿醉后的慵懒。“我得了性病,”王喆的声音哽咽着,“你也去检查一下吧。”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轻描淡写的一句:“Oh,that's a bummer. Just for fun, right?”(哦,真倒霉。不过就是玩玩而已,不是吗?) “玩玩而已?”王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知不知道这会影响我的身体?你必须去检查,必须负责!”她的愤怒在电话里炸开,汤姆却不耐烦地打断:“别小题大做,这种事很常见。”说完就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王喆像活在噩梦里。吃药带来的副作用让她恶心反胃,同学异样的眼光(尽管没人知道真相)让她坐立难安。她一次次给汤姆打电话,从恳求到指责,对方从敷衍到拒接。3月20日晚上,她查到汤姆的住址,揣着化验单冲了过去。 公寓楼的走廊里弥漫着霉味。王喆敲开汤姆的门时,他正和朋友喝酒,看到她的瞬间,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你必须跟我去医院!”王喆把化验单拍在桌上,声音因激动而颤抖。汤姆的朋友开始起哄,有人吹着口哨说“麻烦来了”。 酒精和羞辱让汤姆瞬间暴怒。“离我远点!”他推了王喆一把,她踉跄着撞到墙角,额头磕出了血。愤怒冲昏了王喆的头脑,她扑上去想抓住汤姆,却被他狠狠甩开。混乱中,汤姆抄起桌上的水果刀,朝着王喆挥了过去。 “我只是想让她离远一点。”后来在警局,汤姆对着警察重复这句话,脸上没有丝毫悔意。而王喆,那个三天前还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姑娘,倒在冰冷的地板上时,口袋里还揣着母亲写的纸条,最后一行字是“妈妈等你回家”。 深夜的刘易舍姆区,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寂静。警察拉起黄色警戒线,邻居们隔着窗户张望,没人知道这个亚洲女生经历了什么。担架上的白布被雨水打湿,紧紧裹着那个再也回不了家的身体。 第二天,王喆的死讯像投入湖面的石子,在留学生群里漾开涟漪。有人说她“太不检点”,有人叹“异国他乡太危险”,更多的人只是沉默——那个拖着行李箱、眼里闪着光的姑娘,还没来得及逛一次大英博物馆,还没在图书馆里读完一本书,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永远留在了这个多雨的春天。 她的宿舍很快被清空,书桌上还放着没拆封的笔记本,第一页写着入学日期,和一句工整的英文:“愿不虚此行。”只是这趟旅程,终究没能抵达她想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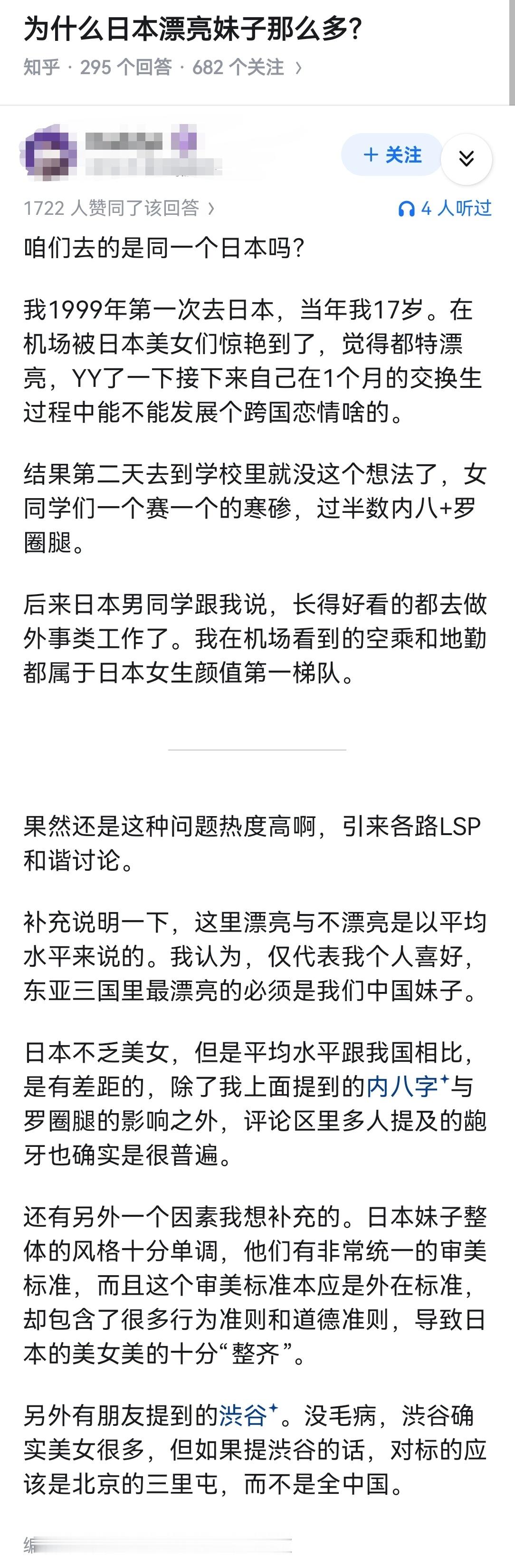






评论列表